
编者按
古典文学的研究,发展至今,已相当成熟,无论是专家之学,还是通人之学,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这并不是说,在理论工具的采用或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可以停止新的尝试。学术的空间无限广阔,研究的视野也同样是无限广阔的。基于这一信念,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或致力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如王同舟《简论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郭皓政《流派视角下的明代诗学论争》,或致力于新的理论工具的采用,如陈庆《古代经济与古代文学》。三位作者用力甚勤,所谈的问题虽然不同,但都努力有所发明。期待学界同人予以关注、指教,以促进相关论述的完善和深入。(陈文新)
作者:王同舟(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当时的评论者无论持赞赏还是鄙薄的态度,他们都清楚,他们谈论的是一种由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派生出来的特殊文体。我们考察明清八股文批评时,同样必须注意八股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把握它在表达形式、理论体系、整体特征等方面与一般文学批评的差别,对明清人的批评意见作出恰当的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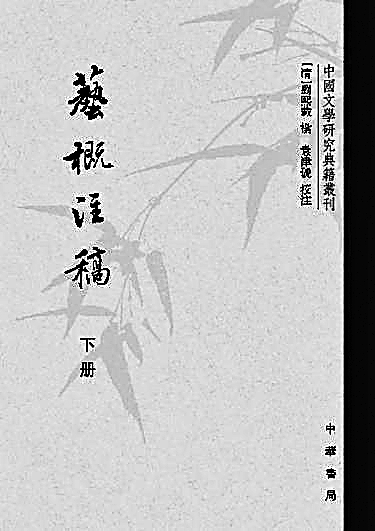
《艺概注稿》 资料图片
或许我们应当首先关心这个批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有的研究者喜欢在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的文集里寻找新异可喜之论,这种做法可能干扰我们对八股文批评体系的整体认知。八股文批评体系最活跃、最有力的参与者是官方。官方的意见以诏令、政书、试录、程文诸多形式公之于世,通过学官、考官的工作加以贯彻,这些或隐或显的“批评”活动,主导着八股文批评的主要论题,影响甚至规范着批评界对各种论题的观点。一般的或者说“民间”的批评界,固然离不开学者、作家,也不乏对官方意见的反驳,然而真正具有声势的,是八股文写作的专门名家、选家和评点家,他们通常借助选本、评本以及经书“讲义”“文法”指南等形式,对官方的主张进行阐释、推衍,引导读者进行创作。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参与者、意见领袖,以及独特的批评表达形式,这些是把握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时需要充分注意的问题。
我们谈到八股文批评体系时,意味着更关注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例如王运熙、黄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等,都提供了体系化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框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明清八股文批评纳入这些框架进行分析。但是,按照传统说法,八股文属于“功令文”,它产生于国家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其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也受到制度的限制。文体自身的特征,造成了相关批评活动明显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为揭示八股文批评的独特性,可将八股文批评理解为由功能论、评鉴论和创作论三个板块构成的体系,三个板块涵盖了官方发出信号到作者响应信号过程中诸多理论和操作问题。
功能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八股文能否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是八股文批评中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从文体渊源上讲,八股文是解经文体,是注疏等解经形式文章化、规范化的结果。文章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增强经义阐发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在考试竞争的压力和中国重“文”传统的引导下,引入文学技巧,强化审美要素。规范化是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性而寻求一个操作性强的统一的基础性评鉴标准,核心是要求行文遵循一定的程式,文中必须加入股对,有骈有散。规范化的实质是把文章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经验提炼出来,作为统一规定,从而使八股文成为一种类似律诗的约定文体。以这种文体作为选拔标准,官方公开的解释是:四书五经系培育人才的根本,八股文可阐发四书五经的精蕴,根据八股文可以衡定士人学问之深浅与人品之厚薄。这里,论证的各个环节涉及文与道的关系、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等文学批评问题,但又不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比如人才标准问题。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争议空间,形成八股文批评中功能论展开的主轴。
由文道关系着眼,赞赏者从八股文性质上立论,声称八股文实现了文道合一;反对八股的人,站在“道”的立场上,指责文章化、程式化的八股文是以文害道,站在“文”的立场上,指责八股文同时破坏了古文与骈文的审美风格,不伦不类。由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着眼,有人赞赏八股文可引导士人深研经典,以圣贤之言沃灌身心,有人说八股都是空言套话,仅是弋获功名之具……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八股取士的声音也来自官方内部。清人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记载,康熙七年曾下诏,“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到次年又诏令仍用八股文章考试;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称“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实不足以得人”,但废止八股的建议不被采纳。梁章钜总结说,“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这告诉我们,对八股文功能的否定,在八股文批评中并不鲜见;对一些批判八股文的观点,也不必一概高估。比如顾炎武曾激烈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日知录》卷十六),但他慨叹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俨然是希望将学校、科举导向培养和选拔精通经史的学者,这就成了远离正解的任性之见。
评鉴论的中心论题是确立评定八股文优劣的标准与方法。在八股取士制度持续存在的前提下,士人对八股文功能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评鉴问题却必须时刻铭记,对八股取士的反对之声,也通常是由对评鉴标准、方法和结果的不满引起的。《聊斋志异》并不在根子上反对八股取士,它一再控诉的是考官无眼,取士不公,反映着社会对“好的”评判标准和方法的强烈期待。乾隆元年,诏令方苞等编选《钦定四书文》,即意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卷首)但是,就提供明晰而统一的“绳尺”和“矩矱”的意图看,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官方始终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评鉴框架。
评鉴论靠着对“文”的构成要素的分析,展开为不同层级的论题、不同观点的论争。在评鉴论中,“义法”“理法”“理法辞气”这些核心概念代表着对“文”的要素的区分,区分出来的要素也成为衡定文章优劣的指标。由于学养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评鉴者优先重视的指标也有不同。例如明末豫章社的艾南英就更重“理”,认为几社的陈子龙等人在辞藻设色上用功,堕入恶道。而在每一项指标之下,仍然存在弹性。比如“理真法老”,是普遍认同的衡文标准。但什么是“理真”,则又有分歧。显然离经叛道的言论应予摒除,但是作者可以“谨遵朱注”,也可以凭借“圣人之言意味无穷”的理由而别出新见,在立场相异的人看来,前者是贪腐嗜常,后者是穿凿附会。“法”的方面同样存在歧义。官方只规定了八股文的基本程式,在符合基本程式的基础上,有人讲究“体方”,有人讲究“机圆”,在他们的反对者眼中,前者可能变成了呆板,后者可能被视为有“凌驾之习”。在评鉴论中,批评者的观点有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但其意图却常常指向影响“选政”,即把带有个人倾向的评鉴标准上升为官方标准,或者将官方标准按照个人倾向进行引申。
创作论的核心命题是怎样写好八股文。创作论以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导士人写作,可以说是八股文批评的真正重心,以致指导士子写作八股文的书籍多如牛毛。因为有关的论述显得琐碎庞杂,理论成分不浓厚,一向很难进入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八股文批评中的创作论不得不如此。晚清刘熙载撰著《艺概》,旨在高屋建瓴地论述诸种艺术,到了《经义概》,也仍要用大半的篇幅讨论细琐的写作问题。细绎《经义概》,可以发现所论的其实是能够推及其他文体创作的工夫。《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个鲁翰林,声称:“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实代表了明清不少人的看法。
明清八股文批评家论创作,总会例行性地谈及读书养气的工夫,这些与一般文论相似。创作论中真正独到的,是对八股文写作过程中“辨题”“入格”“成篇”“成家”各个环节提出操作性极强的指导,创作论也在这些指导中得以展开。明清知名的八股文评论家,像王汝骧、管世铭、路德等人,他们之所以知名,关键在于他们的创作指导能够收到实效;他们论述中体现的那种将写作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将不易捉摸的“风格”等问题纳入字句层面来解决等原则,也蕴藏着值得挖掘的理论因素。
至此,我们可以对明清八股文批评的整体特征加以概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八股文批评中官方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借以维系八股取士制度,使得整个批评体系都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受到政策导向性的影响,八股文批评所讨论的命题相对集中,对命题的看法也难以呈现“百花齐放”的趋势,具有理论的狭隘性。从逻辑和实践上看,八股文批评的重心都在解决如何落实政策,为选拔提供行之有效的标准与方法,为士人提供可依循的写作规范与训练程式,因此,批评中的大量观点,都具有强烈的操作性。与此同时,在这种讲究可操作性的批评中,关于“文”的认识被大大深化了,这应当视为八股文批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