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解志熙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冯至1905年9月15日出生于直隶省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一个败落的盐商之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幼年失母的他性格内向,敏感好学。1921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德文。此时新文学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新文学社团层出不穷。1923年5月,冯至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绿衣人》等诗作而引人注目,应邀加入了浅草社,在该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同时结识了一批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同道,在文艺思想上受鲁迅、张定璜影响较大。1925年夏,浅草社陷于停顿,冯至与好友杨晦、陈炜谟、陈翔鹤等发起沉钟社,成为该社的代表诗人。

这一时期,年轻的冯至贡献出了《我是一条小河》《蛇》等传诵至今的抒情名篇。这些抒情幽婉、想象独特、音韵和谐的爱情诗,给人清新别致的美感。在1923年至1926年间即他18岁到21岁的时候,还接连奉献了四篇相当成功的叙事长诗——《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前三篇“取材于本国民间故事和古代传说,内容是民族的,但形式和风格却类似西方的叙事谣曲。”(冯至:《外来的养分》)《寺门之前》则让一个老僧人自叙其中年时的一次“非常的经验”,以惊心动魄的灵肉冲突表达了人性难抑的痛切申诉。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当时的新诗坛上独步一时,而且此后也一直是他人难能超越的杰作。
1927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冯至远赴哈尔滨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主动接受生活的考验。这次北游也的确开阔了冯至的视野,使他的创作从幽婉的青春抒情转向对社会与人生的现代性思考,其结晶便是1928年年初写成的长诗《北游》。整部长诗构成了一个“游”与“思”互动互补的有机序列,呈现出步步拓展与层层深入的过程,兼具引人入胜的魅力和启人思索的情致。《北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抒情主体的沉吟与咏思,其批判的审视直指畸形繁荣的现代都市和病态的现代人性,诗人两次用“荒原”来象征现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荒芜,这与T·S·艾略特的名作《荒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北游》结束了冯至此前那种浪漫中略带唯美的青春抒情,开启了他此后更为现代性的人生探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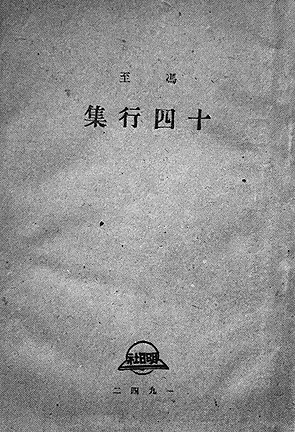
青年时期的冯至为人沉潜低调,为文不喜张扬,所以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坛上一直声名不彰。但文坛巨匠鲁迅在1935年回顾1920年代的新文学时,却出人意料地独推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一个新诗人如此不吝好评,这在鲁迅是很破例的事。历经时间的检验,足证冯至当年的诗作当得起鲁迅的评价。
“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
1928年夏冯至重返北京,在孔德学校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在这期间,得以聆听著名学者宫多尔夫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倾心于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领受了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哲学的洗礼,冯至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创作态度更趋严肃,只有少量作品在国内发表。
1935年6月,冯至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启程回国,途径巴黎与交往七年的女友姚可崑结婚;9月归国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7月赴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南迁浙江金华、江西赣县等地。1939年暑假后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经过1930年代整整十年自觉的沉潜与磨炼,人到中年的冯至在创作上迎来了又一个丰收期:1941年他创作了27首十四行诗,编为《十四行集》于次年出版。该集以深沉的情思、精湛的诗艺,获得了诗坛的赞誉,被李广田推许为具备了深度品质的“沉思的诗”、被朱自清肯定为中国新诗由不免肤浅的青春抒情进入成熟的中年沉思之标杆;同时,冯至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凡的造诣——历史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以及一系列感时论事析理的知性散文如《决断》《认真》等篇,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收获。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1940年代的冯至也逐渐地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转变。
最重要的创获当然是《十四行集》。《十四行集》悉心表达的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与生命感怀,而达到了非常精深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人这种存在者之生死悖论的思索与生命意义的探询,对个体存在的孤独性、有限性的自觉沉吟和对存在者相互关情、相互敞开以至于生死共在之境界的庄严歌咏,由此诗人着力弘扬一种严肃生活、勇于承担、多所关怀和敢于开拓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诗,其严肃凝重的艺术格调和深邃精微的思想深度,不仅在中国新诗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显示出诗艺的成熟。
十四行是西方诗歌中格律最为严谨的诗体,在冯至之前的中国新诗人也曾尝试运用,但都不大成功,加上极端的形式自由主义一直被人奉为新诗艺术的信条,所以当时不少人都认定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十四行体移植到中国。冯至从德语诗人里尔克情思深湛、艺术精湛的变体十四行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受到启发,“渐渐感觉到十四行与一般的抒情诗的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题有后果,有穿梭般的韵脚,有一定数目的音步,它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冯至:《我和十四行的因缘》)这让冯至感到十四行体与自己的生命体验恰好契合——“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冯至:《十四行集·序》)的确,十四行体与冯至的“思、想”如此相得益彰,堪称完美的结合。
同时,冯至也自觉地从中国古典诗艺如律诗中吸取了艺术营养,如有一首十四行的跨行对句“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分明有杜甫七律《登高》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回响。《十四行集》的出现,把中国新诗提高到可与最完美的中外古典诗歌相媲美的水平,鲜明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并在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的诗学思维来拓展中国古典诗歌的“言志”“寄托”传统方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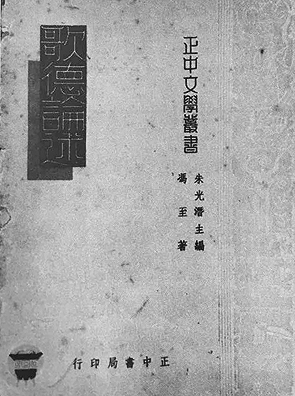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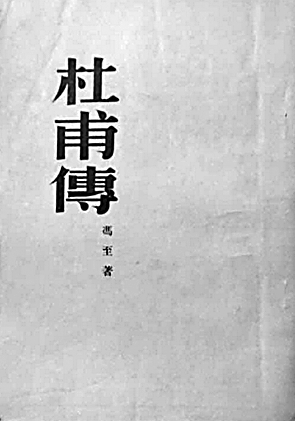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机体来研究”
在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的急风暴雨中,人到中年的冯至体念时艰,欲以学术报国,因而沉潜钻研,学术大成。
作为诗人学者的冯至精心选择了中西两大诗人杜甫和歌德作为专攻对象。抗战时期的冯至与杜甫一样身经国难,这使他深切地感到:“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冯至:《赣中绝句四首》之二)。所以,冯至对杜甫的诗有特别深切的体会,于是他深入钻研文献,努力为杜甫写一部准确可靠的研究性传记,并在194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杜甫传》的大部分章节,1950年代初又重写全稿、连载于《新观察》杂志,1952年结集为《杜甫传》出版。作为留德博士的冯至对德国大诗人歌德的热爱也是由来已久,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他得到了两套完备的德语版《歌德全集》和《歌德年谱》,爱不释手、朝夕研读,于是精心选择若干重要问题纵深开掘,撰写发表了六篇专论,1948年结集为《歌德论述》出版。
《杜甫传》和《歌德论述》一出版就被公认为代表了现代中国的杜甫研究和歌德研究学术水平的扛鼎之作,就现代人文学术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两部著作也堪称典范性的标志之作。诚如冯至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这工作,在西洋十八世纪时已经开端,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经长成……但是在中国,这部门的书架上几乎还是空空的。”(冯至:《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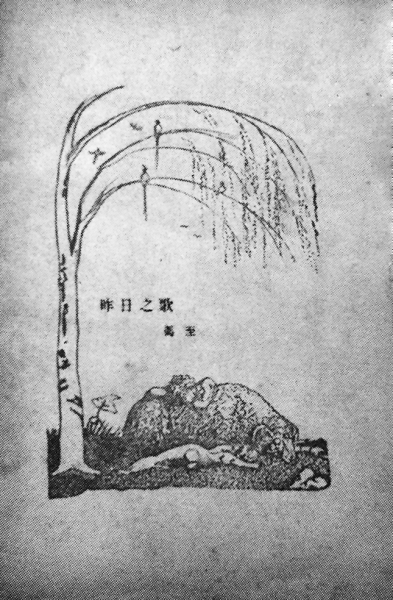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诚然,昔人关于杜诗的注解、考证和诗话数量繁多,但长期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著述;现代学人关于杜甫的考论也为数不少,但颇嫌零碎,一些传记大都浮光掠影而不及深入。同样的,现代中国文坛对西方经典作家如歌德的翻译也颇多,学者的论述则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铺陈,鲜见深造自得的专深研究。
冯至的《杜甫传》和《歌德论述》之所以颖然秀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趋于成熟的代表论著,与冯至过人的文学和学术修养分不开。冯至本身是杰出的诗人,自然对杜甫和歌德的诗与人深有体会,而冯至留学德国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尤其是主导了德国人文历史学术的兰克学派的学术方法,与冯至从中国古典学术所继承的语文学、考据学方法相得益彰,再加上来自鲁迅思想和德国哲学的启发,以及左翼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积极影响,如此等等的学术与思想方法之交汇,使冯至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既具有艺术的敏感体悟和学术的严谨求实,又具有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深入的思想洞察,所以才能超越一般、成就杰出。
由于冯至在文学和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学术界和文学界都肩负重任,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后来又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兼任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工作中国语言文学组组长,为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教学及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至同时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全国文联委员以至全国人大代表。在繁忙的教学与社会工作之余,他继续诗歌创作、受命参与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旧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冯至对蒸蒸日上的新中国满怀热爱。“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冯至作为资深诗人和学术权威,自然难逃冲击与批斗。进入新时期,已是暮年的冯至欣感身心的解放,积极领导了外国文学学科的重建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复兴,同时这位文坛前辈也创作不辍,直至1992年,88岁高龄的他仍有诗作和译诗发表,为自己70年的文学生涯划上一个沉稳的句号。
冯至一生自觉地承担生命、深入地体会文学,始终坚持严肃地为人与为文,既在创作上卓然成大家,诗歌与散文成就尤为杰出,又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和成就卓著的文学翻译家,他对德国文学的翻译已成译品之经典,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滋养了许多中国作家,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被公认为卓越的学术界碑。冯至的文学和学术遗产,必将传诸久远。
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等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十四行集》第一首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学人小传】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省涿州市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0年留学德国,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
冯至20世纪20年代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登上文坛,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小说《伍子胥》影响深远。他的杜甫研究卓然成家,其德语文学研究、教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国际性的肯定和赞誉,先后被聘为瑞典、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得诸多国内外奖项。
新发现的冯至佚文——
决断
一个青年朋友,认真而诚挚,没有幻梦,他知道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是怎样腐朽而陈腐,但他的净洁的目光好像望着一个更深一层的真实,让那些陈腐不和他发生纠葛,多少琐碎而卑污的事对于他也就无能为力了。去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他觉得他应该应征,可是他同时也明瞭,中国现在的军队大部分生了锈,发了霉,他不知道人家将要怎样训练这批新鲜活泼的青年。从军,是他内心的命令;事实的状况使他犹疑,给他坦白的心蒙上了一层云翳。他于是不能不考虑,他经过几日夜的思量,终于决定了,还是服从内心的命令,不管现实可能是怎样腐败。我听说,他考虑时很苦恼,决定后却感到无上的快乐。他这从考虑到决断的过程,有如经过长久的春阴终于见到灿烂的阳光,十分美丽。他入营后,我在他的纪念册上写过这样一句:“人生的意义在决断里。”
我们自从“九一八”后,人民抗战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生长,在这中间那些衰老的、怯懦的、狡猾的官僚们我们姑且不论,一部分所谓老成持重的人尽在考虑着我们的实力到底能不能抵抗敌人,还有少数的聪明之士在报纸上发挥“敌乎友乎”的高论——这样在侮辱中议论纷纭地过了几年,直到“七七”那一天来抗战的情绪达到最高点,庐山会议决定不顾一切的利害,展开全面抗战,这好像郁闷了许多日子,忽然落下雨来,人人都深深地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虽然我们后来抗战的成绩并不很高明,暴露出许多民族的丑态,但回想起我们决定抗战的那一天,是我们民族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一个最美丽的日子。
在决断时,无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多半是走到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可能道路前,不能前进,要加以选择。这时不能前进了,需要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梗在他面前,绝不会有另外一个人或是另外一个民族走来,告诉他走那条道路为宜,更不会在天空中显露出什么神的启示,这时他感到绝对的孤单。这种感觉,动物是没有的,它只是盲目地走上一条;原始性的人也很少有,他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多半求神问卜,让神或卜给他解决。只有自己对于自己负着责任的人在这里才既不盲目,也不依靠神卜,他要自己决断。人生面对着不同目的道路,孤单地考虑自己应该走那条道路时,才会体验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等到他决断了,勇敢地走上一条,这时他所能感到的生命的光彩也不是一个动物或一个原始性的人所能感到的。所谓人生的意义多半也在这一点上。丹麦思想家基尔克戛尔特说:“选择把一种庄严,把一种永久不会失却的寂静的尊荣,赋予一个人。”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
在世界文学中许多伟大的作品都善于描叙政治彷徨的苦恼。丹麦王子在《哈姆雷特》第三幕里的独白,提出“生,还是不生——这个问题”,成为千古的绝唱;屈原在《卜居》里说尽他胸中的矛盾;浮士德内心里两个灵魂的冲突主宰着全悲剧的进程:谁读到这些地方,对于这种可此可彼、何去何从的问题不感到深切的同情呢?但文学只写出这个现象,并没有回答,如果你不肯滞留在这只是同情上边,便立刻在文字之外会听到一个更雄浑的呼声:“你要决断!”这个呼声也许使懦者不敢向前,使强者凛然生畏,但在凛然生畏中含有极沉重的人生的意义。
生,需要决断,不生,也需要决断。一个人对于事业,对于爱,若是走到最艰难的段落上,便会在自心内发生严重的问题:继续追求呢,还是断念?可是追求需要决断,断念也需要决断。在这样的决断前或许使人感到难以担当的艰难,但是非克制这个艰难不能得到新的生命的发展。孟轲以他伦理学家的口吻用鱼与熊掌的取舍比喻生与义的取舍,但事实上后二者间的取舍绝没有前二者的取舍那样轻易——这样,越是艰难的,其中含有的意义也越重大。
对于在生活里不发生需要决断的问题的人,根本提不到幸与不幸。人间的不幸者却是那些已经发生问题而又不能决断的人,以及已经决断,才向前走了几步,随后又懊悔这个决断的人。俗话说,提不起来,放不下去,这境界是苦恼的;但是决定把事物放下了,一转念又想走回来把它提起,是更为苦恼。前者使生命停滞,后者使生命浪费。这样弄来弄去,总不免要讲一出平凡的悲剧。歌德在一部小说里说过这样的话:
按照我的意见,决断是人类最值得尊敬的事物。货物与金钱人们不能同时兼有——有人不肯花钱只永久渴望着货物,有人货物买到手了,又懊悔花了钱,二者是同样地不幸。
买一件东西,当然是小事,但是对于自己切身的问题也陷入这种境地,那么在这样的人面前将要永久呈露不出生命的光彩。
【整理附记】
这是新发现的《决断》初刊稿,载昆明《自由论坛》第24期,1945年4月21日出刊。文章开头说,“去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动于1942年,则此文当写于1943年。“决断”即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观念。在抗战的艰难时刻,冯至语重心长地鼓励国人:无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都要勇于决断并坚持到底。《决断》后有增订稿、载北平《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出刊。
——解志熙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