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科技】
撰文 道格拉斯·T·肯里克 亚当·B·科恩 斯蒂芬·L·纽伯格 罗伯特·B·查尔迪尼 翻译 红猪
公众对不同的科学发现往往有截然相反的反应。新型飞机和新款手机一经问世就收获满堂彩,而质疑政治或宗教现状的发现就可能遭到诘难和反对。
如何说服公众接受那些有确凿证据的研究?光是喋喋不休地罗列事实显然不行。实际上,这样做还可能适得其反。由于人类天生就存在认知偏差,在做决策时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近来,心理学家发现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一些关键障碍,比如走心理捷径、固执己见、从众心理,他们针对每种情况,都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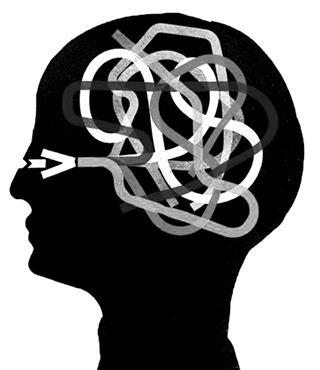
1.认知偏见
从原则上说,科学研究应该远离派别之争。毕竟,科学研究是通过验证关于自然界运行原理的各种假说来得出结论的。以鼠海豚为例:根据它的外表和水栖特性,这种动物应该是鱼。但是,科学家却多方搜集证据,打破了这个成见。观察它的骨骼结构,发现它没有鱼鳃。此外,它还与其他温血陆地动物有许多共同基因。因此,科学家很肯定地将鼠海豚归为了一种哺乳动物。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事实,却并不像确定鼠海豚是不是鱼一样容易让人达成一致。这一点,只要看看网上的新闻就知道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还有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一百多年来有关进化论的证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学院知识分子给“科学”两字打上了引号,而许多非专业人士又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反科学的认知偏见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近几十年来,关于私藏枪支的相关研究,从美国政府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全美数百个城镇举行游行呼吁控枪。 新华社发
公众对科学发现的态度是摇摆的:对于新型汽车和新款手机,大家笑脸相迎;而当科学发现挑战了现行的政治或宗教观念时,公众又会同样迅速地萌生敌意,历史上案例太多了。在伽利略的时代,罗马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其实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主张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当伽利略公布他的观测结果,质疑当时的主流学说时,他们却出离愤怒了。伽利略遭到软禁,被迫将自己的观点当作异端放弃。
原则上讲,科学思维就是尽可能得到和某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旦科学家发现,某些论点没有牢固地建立在逻辑和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证据上,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要么不了解事实,要么就是出于私利的目的在阻止事实的传播——比如,某些烟草公司压制吸烟和肺癌相关的研究成果。面对缺乏理性或者怀有偏见的对手,科学家的嗓门常会越来越高,会更加高调地说明事实,希望自己的对话者也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反科学的认知偏见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近几十年来,关于私藏枪支的相关研究,从美国政府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全美数百个城镇举行游行呼吁控枪。 新华社发
然而好几方面的研究都显示,喋喋不休地罗列事实未必能让对方作出更客观的决策。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还可能适得其反。虽然人类是智慧生物,但可惜的是,在做决策时,我们并非完全理性。
要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非理性思维,需要综合好几个领域的科学知识。本文的四个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

特朗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出于私心成见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图为美国洛杉矶举行“人民气候游行”。新华社发
查尔迪尼熟知启发法(heuristics),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迅速决策的法则。
肯里克研究了我们的决策是如何被一些社会性动机(比如寻找配偶的欲望或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扭曲的。
科恩研究了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的判断。
纽伯格研究的是认知偏见,它会使人在遇到新的相反的证据时坚持原有的观念。
我们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深入理解扭曲理性思维的心理学机制。
大家经常受到错误观点的误导,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以正视听至关重要。我们和同行的研究指出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关键障碍。我们探讨了这些障碍为什么产生,我们该如何与它们抗争,并最终将它们击垮。在所有这些障碍中,有3种特别突出:
思维惯性。人脑天生就有一种对付信息过载的策略:当我们的信息太多,或者时间太少时,就会依赖一套简单的“启发法”来做出决策,比如接受群体的共识,或者信任一位专家。
私心成见。即使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兴趣,不用走捷径,我们有时仍会以有失偏颇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时的我们不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倒更像一个为暴民代言的律师。我们天生有一种倾向,会关注某些发现,忽视另外一些;会重新解释复杂的证据,使它们符合我们的固有观念。
社会动机。就算我们克服了前两个障碍,强大的社会动机仍会阻挠我们对既有信息做出客观分析。我们会偏向哪种科学结论,取决于我们有着怎样的社会动机,比如是否渴望获得社会地位、和某个社会群体观点一致、追求一位伴侣。
2.思维惯性
要精通科学,你必须掌握一套深奥的概念。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例。要理解它,你必须先理解一整套逻辑前提:有限的资源偏好那些善于获得食物、住所和配偶的个体,这会导致性状的选择性出现,从而将这些技能传递给未来的世代。学习达尔文理论的学生,还必须了解一些比较解剖学(他们要知道,在骨骼结构方面,鲸和人类的相似程度要大于和鱼类)。另一个必备条件是熟悉生态学、现代遗传学和化石记录。
尽管自然选择是科学史上证据最扎实的理论之一,但普通公民并没有精力读完那些写满证据的教科书。实际上,就连许多在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甚至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博士,都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演化生物学的课程。因为有了这些障碍,大多数人就只能依靠思维惯性或是听从专家的声明了,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将他们引上歧路。他们还可能依赖直觉,这也会误导他们。
我们使用启发法是因为它们常常很有效。比如一台电脑出了故障,用户可以用几个月熟悉其中的电子元件和它们的连接原理,也可以直接去问一名电脑技术员。如果一个孩子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他的父母与其研读医学文献,不如直接咨询医生。
但有时,走捷径却会对我们不利。1966年,精神病学家查尔斯·K·霍夫林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当人们把“博士”头衔当作个人权威的象征时,事情会发展到怎样糟糕的地步。实验中,几个在病房中忙碌的护士接到了一名男子的电话,男子自称是某个病人的医生。他在电话中要求护士到药箱里去取一种名叫“Astroten”的非常用药物,并以每天最高剂量的两倍给病人服用,这不仅违反了药物标签上醒目标注的使用须知,也违反了这家医院要求医生手写处方的规定。这些护士会犹豫吗?她们中的95%都毫不质疑地服从了这个所谓的“医生”(英文中“医生”与“博士”是同一个词,编者注)。甚至当她们拿着这种有潜在危险的药物走向患者的病房时,研究人员需要强行阻止才能把她们拦下来。这些护士在无意间使用了所谓“权威启发法”,即轻易相信了一个身居要职的人。
3.私心成见
当我们对某个话题十分关心,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它时,我们就会超越简单的启发法,开始对切实的证据开展更加系统的分析。但是,就算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立场维持客观,也仍可能受到既有知识的阻碍。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会对强化自身观点的论据特别注意,不喜欢反对意见,也容易厌恶那些立场和自己现有观念发生冲突的人。那么,如果一个聪明人被迫思考正反两方的证据,结果又会如何呢?
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洛德和同事开展了一项研究。参与研究的自愿者都是斯坦福的学生,照理说应该很擅长对科学信息做出合理判断。研究人员给这些学生看了几轮关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的科学证据,比如先让他们阅读一段文字,文中描述的研究质疑了死刑对预防严重犯罪的效果。研究比较了美国14个州在启用死刑前后的谋杀率的变化。其中11个州的谋杀率在启用死刑后反而上升了,这说明并没有起到威慑效果。
接着,这些学生又听其他科学家指出了这项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然后由原来的研究者反驳。在这之后,学生们又听说了一项得出相反结论的研究:死刑确实能预防犯罪。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比较了10对死刑法律各不相同的相邻州的谋杀率。其中有8对数据显示,谋杀率随着死刑的执行而降低,这个结果支持了死刑。接着,学生们又听到了对这个研究的质疑,以及对于质疑的反驳。
照理说,如果学生们一开始是怀着强烈的观点参加实验,那么在对事实做了一番冷静理性的分析之后,他们的观点应该会趋向于中立,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各种证据,其中的科学观点对于死刑的废止有支持也有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过一番辩证之后,之前赞成死刑的学生现在更赞成了,之前不赞成死刑的更反对了。显然,两边的学生都没有公正地处理这些信息。相反,他们认为强化自身立场的那些证据更加有力,而对这些证据的反驳都是软弱无力的。可见,虽然我们看似公正地对相反的观点也进行了审查,但衡量这些观点时,会不由自主地戴上有色眼镜。
最近,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安东尼·N·沃什伯恩和琳达·J·斯基特卡开展了一项研究,似乎也支持了斯坦福大学这篇论文的发现。两位研究者检验了一种说法:美国的保守派比自由派更不尊重科学证据,或许是因为前者思维僵化,不容易接受新的体验。然而,研究者发现,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会拒绝违背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的科学发现。他们向1347名参与者展示了关于6个热点问题的科学证据,包括气候变化、枪支管控、医保改革、移民政策、发展核能和同性婚姻。乍一看,这些研究似乎支持了辩论的一方(比如,实行枪支管控的城市犯罪总数更高),但是仔细考察数据后就会发现,内容支持的是题目相反的观点(比如,在实行枪支管控的城市,犯罪数减少的比例要高于不控枪的城市)。
如果粗看一下这些数据,就符合反对控枪团体的期望,那么这些团体的成员就会满足于符合他们偏见的发现,不再仔细追究了。要是结果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些枪支鼓吹者就会仔细检查研究中的细节,直到发现那些支持相反结论的数字。
如果研究者后来告诉那些团体的成员,研究结果支撑的是与他们对立的观点,那么这些成员就可能对开展研究的科学家产生怀疑。
4.社会动机
社会冲动能帮助我们与人和谐相处,但它们同样也会成为阻碍我们理性思考的巨大障碍。试想一场办公室里的聚会,你的同事正高声发表关于进化论、全球变暖或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谬论。面对这个情形,你是会站出来反对,还是一声不吭,避免破坏和谐的社交氛围呢?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对“从众”这一概念始终非常感兴趣。1951年的一项对“群体动力学”的经典研究中,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指出,如果一个人反对群体共识,就会遭遇这样的下场:群体会先尝试改变此人的观点,一旦失败,他们就会中止沟通,将这个异类孤立在群体之外。2003年,现就职于普渡大学的吉布林·D.威廉姆斯和同事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受到排挤,他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就会激活——这也是我们感觉身体疼痛时就会激活的皮层。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经济学教授格利高里·伯恩斯和同事领导的团队发现,和自己所属的集体意见相左时,杏仁核的活跃程度会增加,而这个区域一般会在人受到各种压力时激活。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意见相左,是一件让人在情感上很受伤的事情,即使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人们不愿提出相反的证据来驳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观念,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除此之外,社会压力还会影响我们对既有信息的处理。当所属群体已经达成共识,人们会更倾向于使用启发法,或接受已有的观点,而这些都会妨碍人们的客观思维。
我们自己的团队也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先让受试者从美学的角度对一系列抽象图案和画作进行评价,然后让他们阅读一段文字,使他们进入一种自我保护,或是比较浪漫的心境。
在前一种场景中,受试者会想象自己独自在家,被一声巨响惊醒。随着情节展开,受试者渐渐明白有外人闯进了房子。他们会想象自己伸手拿起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断了。他们大声呼救,却没人应答。忽然,卧室门被猛地撞开,一个陌生的黑影赫然出现在眼前。
另一种情况下,受试者会读到一段关于浪漫邂逅的文字,他们会想象自己外出度假,遇见了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和对方共同度过了浪漫的一天,最后以激情之吻画上句号。
接着,受试者来到一个虚拟聊天室,和另外三名受试者一起评价几幅抽象图片。其中有一幅图片,受试者曾经看到过,他认为还算有趣,但在这次评价中,他得知其他三个人对这幅图片的评价远低于平均值。
这时,受试者会改变原来的评价,以迎合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吗?受试者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一种场景中的受试者更容易服从集体的评价,而读到浪漫故事的受试者,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女性会服从集体,而男性的评价却和集体相反。
我们团队在其他研究中发现,恐惧通常会使男性和女性都服从集体的意见,而性爱动机则会促使男性从集体中脱颖而出——或许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合格的配偶吧。这时的男性会持相反的意见,让自己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受试者的观点都受到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目标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在处理既有信息时并不是完全客观的。
5.应对方法
既然人类的思维中有这么多阻挠理性思维的障碍,我们是否该放弃抗争,承认无知和偏见才是最后的赢家?当然不是这样。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家已经分别针对启发法、私心成见和社会压力,提出了应对的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当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强烈的兴趣仔细考察证据时,常常会依赖捷径,即简单的启发法。但是,这种经验法则常常可以通过简单的干预来破除。研究市场营销的学者约瑟夫·W·阿尔巴和霍华德·马莫尔施泰因做过一个实验,要求受试者考察两款相机的12项功能。其中A品牌只在4项功能上比B品牌优越,但这些功能都是决定相机品质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比如曝光精度。B品牌的推荐语则说,它在8项功能上更加优越,但那些都是次要的功能,比如配有肩带。参与者分成了两个组,一组对每项功能只有两秒的研究时间,另一组则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全部功能。
当受试者考察每项功能的时间只有两秒钟时,只有少数(17%)会选择那款高品质相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拥有次要功能较多的那款。但是,当受试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直接比较两款相机时,超过2/3的人都选择了功能较少,但整体品质更高的那款。这个结果说明,在给出复杂证据时,如果想让对方从启发法切换到系统的思考模式,以做出更客观的整体评估,充裕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私心成见常常可以通过改变立场来克服。前面提到的几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不仅考察了人们对死刑的态度,还研究了如何改变这些态度。他们先是指导一些学生制定了一个和死刑有关的假想决策,要求决策过程保持客观,并公正地衡量证据。但这个要求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要求另一些学生自己跟自己唱反调,要他们设想,如果关于死刑的研究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将做何评价。这时偏见一下子消失了。学生们不再用新的证据来维护他们既有的偏见了。
消解社会压力的一种手段是,先探明群体内部是否真的达成了一致。有时,群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反对错误观点,就能使其他成员敞开心扉。《科学美国人》曾在1955年刊登过一篇文章,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E·阿施在文章中介绍了对从众心理的几项研究,他发现只要群体中有一个人和多数人意见不同,“共识”就会瓦解。同样,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那几项著名的服从研究中(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受试者相信自己正在电击心脏病患者,使其感到痛苦),只要群体中有成员不听命令,盲目的服从就会消失。
恐惧会加重从众的倾向。如果你想劝说别人减少碳排放,就需要先谨慎地考虑对方的情况:如果听众本来就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那么激发他们对黑暗未来的恐惧或许会很有效果,但如果听众本来就怀疑气候变化,这样的恐吓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上面的几点简单建议,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克服那些阻挠客观科学思维的心理障碍。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如何说服别人、提高社会影响力的书,如果你想和某个群体沟通,而这个群体的信念又公然违背了科学证据,那么你大可以利用此类资料。但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必须用更加系统的方法搜集数据,找出在某些问题上与反科学思维对抗的有效策略。关键是要弄清楚,一个人为什么拒不接受确凿的证据,是因为对方使用了简单的启发式思维、存在确认偏误,还是有什么特定的社会动机?
这些针对非理性思维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反科学的信念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导致公众不能充分理解那些可能影响公共福利的重要现象。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关于家中藏枪和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从政府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而事实上,有枪的家庭常会出现青少年自杀的案件,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刻不容缓更是科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
对新奇的科学发现持怀疑态度是人的天性,对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感到沮丧。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乐观的理由:今天,伽利略的大多数意大利同胞,甚至教皇本人都已经接受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事实。达尔文的大多数同胞也都认可了进化论,英国国教的公共事务主任甚至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我们相信,如果科学家能充分利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了解是哪些认知偏差在阻挠理性思维,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接受客观的证据,了解自然界的运行原理。
本版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