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序跋】
作者:肖复兴
我5岁那年,生母去世。对她,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前些年,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的自传——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是在大栅栏的同乐电影院看的,便记住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也是5岁那年生母去世。在那本自传里,她说自己还清晰地记得,当初离开家跟着继母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同样是5岁,为什么她记得这么多事情,而且记得如此须眉毕现?
这让我非常惭愧。年老之后,常会回想母亲的样子,很希望能像高峰秀子一样,搜寻出胶木奶嘴之类的细节来。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母亲的样子,总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母亲的样子,是和姐姐的模样重叠的。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对姐姐的思念。为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姐姐离开北京,只身去了内蒙古参加京包线的铁路建设。那一年,姐姐才17岁。

老槐树旁的旧居 肖复兴绘
1989年夏天,继母去世。那一年,我42岁。生母去世之后不久,继母便来到我的身边,和我相依为命生活了37年。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和她一起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15年,艰辛与共,相濡以沫。我对她的了解和感情,比生母要多。
1989年底,我写了一篇《母亲》,写的就是继母。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发表在次年第一期的《文汇月刊》。1992年,这篇作品由孙道临先生出任导演搬上电影银幕,郑振瑶扮演我的继母。
1994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散文集《情丝小语》,书中收录了《母亲》一文。我将书寄给孙犁先生。没有想到,孙犁先生读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鼓励有加的信:
复兴同志:
您的信来得快一些,我发信,是托人代投,有时耽误。
您的书,我逐字逐句读完第一辑,其他选读了几篇。在这本书中,无疑是《母亲》和《姐姐》写得最好。
文章写得好,就能感动人;能感动人,也就是有真实的感受,就是有真实的体验。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能遵循的人,却不多,所以文学总是无有起色。
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你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这篇文章,我一口气读完,并不断和我的身边的人讲,他们有的看过电影。当年《文汇月刊》我是有的,但因很少看创作,忽略了。又不看电影。
现在有的作家,感受不多,感想并不少,都是空话,虚假的情节,虚假的感情,所以,我很少看作品了。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读到这样一篇好文章,并希望坚持写真实,不断产生能感人的文章。
即祝暑安!
孙犁
七月四日上午
孙犁先生的这封信,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到,母亲和姐姐都写过了,唯独没有写父亲。我很想写写父亲,几经颠簸,却无从下笔。相较于母亲和姐姐,父亲,我是不大了解的。
孙犁先生在信中所说的关于父亲的那段话,当时我看了只是感动,并未真正理解,更未深思,尤其是那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我没有认识到孙犁先生话中的含义。囿于年龄,对世事的认知、对人的理解,哪怕是你觉得很亲近的家人,往往并不透彻——涉水未深,却自以为五湖阅尽。那时,我已人到中年。
经年之后,特别是人老之后,孙犁先生所说的“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这句话,再次盘桓在心中,写父亲的念头也再次涌出。重新钩沉从小到大和父亲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很多记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除了唤醒沉睡多年的回忆,还需要打捞不少已经失去的记忆。那些记忆,之所以失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在于自己对世事、人心、人性的认知。这不仅仅在于记忆力的好坏,更在于思想和情感。很多失去的记忆,是被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筛子有意或无意地筛掉或回避的。柯林伍德说的“过去的思想”重新唤醒我们的能力,就是对那些浅薄甚至错误的认知进行清理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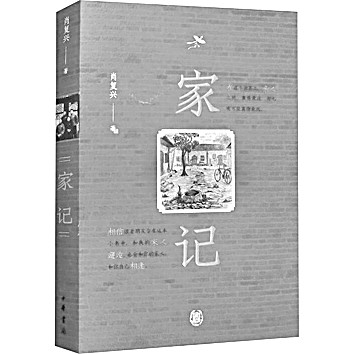
《家记》(肖复兴著)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种被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记忆,在今天有着很大的价值与意义(太顺畅的回忆,只是温柔的抚摸),它们能够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连接起来。这个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过程,需要自己勇敢地去面对:面对父亲,面对时代,更面对自己的内心,特别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的浅薄、懦弱、过失所缠裹形成的思想与情感。对于晚年的我来说,这是痛苦的,也是有益的、值得做的事情。
当我渐渐变老的时候,我和父亲才一点点地接近,这让我付出了几乎一辈子的代价。而这时,父亲已逝去多年。我这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之间,看似离得最近,却也可能离得最远。
2015年夏天,我终于写出了《父亲》。这一年秋天,带着三万余字的初稿,我去美国看孩子。2016年的春节期间,在清静的小城布卢明顿,我将《父亲》修改完,发表在201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至此,《姐姐》《母亲》《父亲》都写完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从人生还是文学上来看,这都是三篇重要的作品,我敝帚自珍。从1989年到2016年,经过了27年,终于写完了,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一年,正是我七十初度。
记得那年正月初七,最后改完《父亲》,关上手提电脑,走出房门。屋外大雪纷飞,漫天皆白,眼前一片迷蒙。恍惚中,不知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感谢中华书局的美意,除《姐姐》《母亲》《父亲》这三篇,意欲将这些年我写的关于家的零散文字集成一书。便又加紧补写一些篇章,特别是关于弟弟和儿子、孙子的篇章,集成四辑,“四世同堂”,从而使一个家比较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算一算,从最早写《母亲》的1989年,到本书最后一篇写关于孙子的《游泳记》的2023年,居然前后经过了34年。一本小书,一个作者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是和日子一起长大的。对于我,这是绝无仅有写了这样长时间的一本书。
过去常说“家国情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家和国不可分开,没有国,便没有家。同样,没有家,便也没有国。家是国的细胞,家的微观史,是国和民族的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连自己的家都不甚了了,对国就很难说得上有很深的了解和感情。一滴水,哪怕是极为平常,甚至浑浊的一滴水,也可以折射蓝天白云和太阳的光辉。这本小书,便是这样的一滴水,其中不仅仅有几代人的亲情,更有近一个世纪的世事沧桑,充满人生况味,苦辣酸甜、聚散离合、生老病死……我家如此,你家或许也大同小异。相信读者朋友会在这本小书中,和我的家人邂逅,也和你的家人以及你自己相逢。
我将这本小书取名为《家记》,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名字,如同我们简单朴素的家。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记”,即使你没有写出来,它也记在你的心里。
(本文为散文集《家记》自序)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9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