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姚泽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当今医学技术飞速发展,诸多疾病不再致命。这些成果的背后,传统医学经验功不可没。回首人类与疟疾旷日持久的抗争之路,“双药”(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后来实现人工合成的奎宁,以及从青蒿中低温萃取的青蒿素)的作用举足轻重。其背后,是药品研制的艰难跋涉,是传统医药知识向现代跨越的崎岖转型。科普作家梁贵柏在《双药记》中,挥动生花妙笔,带我们回溯这场跨越时空的人类与疟疾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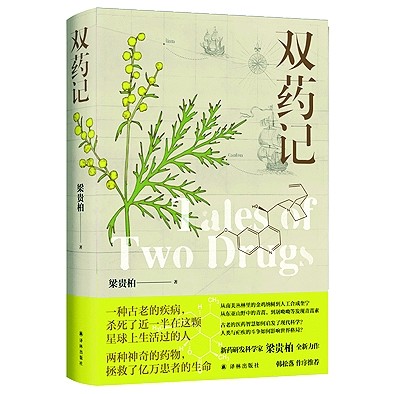
《双药记》 梁贵柏 著 译林出版社
全球史视野下的疟疾与“双药”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是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寄生虫感染。据估计,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人类,近半数都因疟疾而失去生命。这种跨越洲际的致命威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疾病肆虐中愈发清晰。正如全球史先驱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揭示的,历史学不能忽视人类与疾病相互影响的历史,疾病常常影响甚至左右世界历史的进程。
《双药记》正是将人类抗疟历程置于全球史框架中审视。近代以前,东西方各自探索抗疟方法:中医典籍记载的常山、马鞭草,与美洲印加人的金鸡纳树皮,构成平行时空下的智慧结晶。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抵达广州,打破了这种独立状态,欧洲人将美洲金鸡纳树皮奉为“神药”并传至全球。科研人员从中提取分离出活性成分奎宁,康熙皇帝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该药治愈疟疾的人之一。
20世纪初,奎宁生产形成全球合作的工业化体系。1913年《奎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首个跨洲际制药垄断联盟(涵盖亚非种植园主、欧洲制造商及荷兰等殖民国家)的诞生。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奎宁是维持殖民统治的关键,若无此药“也许早就分崩离析”。
但“二战后,疟原虫对奎宁及其类似药物的耐药性成了全球疟疾防控的最大问题之一”。真正改变抗疟格局的是青蒿素的诞生。越南战争期间,耐氯喹疟疾肆虐促使胡志明向中国求援,中国科研团队启动“523任务”,最终发现青蒿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全球社会,推动青蒿素药物实现量产并走向世界,为全球抗疟事业注入新动力。
从美洲金鸡纳树皮到中国青蒿素,两种药物的全球传播史印证了该书的观点:人类在疾病面前唯有共享智慧、协同行动,才能书写命运与共的全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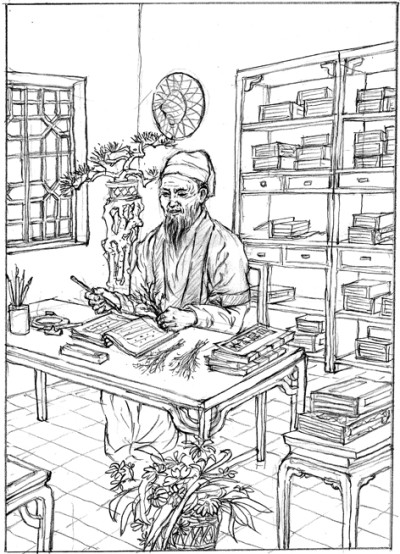
李时珍潜心编撰《本草纲目》 任坚 绘
“双药”诞生背后的艰难征程
回首疟疾与“双药”的全球史,那波澜壮阔的历程令人感慨。而这背后,药品研制之路更是荆棘丛生,充满艰辛。例如推动青蒿素转化为临床治疗药物的一个关键人物——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为了比较各种药物和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在1969年主动感染疟疾,然后告诉其他科研人员“各种方案可在我身上进行试验”。
然而,科学的进步以及新药的诞生,所仰仗的条件又绝不仅局限于此。一方面,在科学探索的漫漫征途中,从来不缺各式各样的“机缘巧合”与“意外之喜”。举例来说,16世纪时,远赴南美的意大利传教士萨伦布里诺留意到当地原住民巧用金鸡纳树皮来抑制颤抖、消退高热,他灵机一动,寻思着:为何不尝试用这些树皮去医治疟疾呢?就这样误打误撞之下,当时最为有效的疟疾特效药问世了。青蒿素的发现历程,同样充满偶然性。彼时参与“523任务”的科学家多达500余人。可难题在于,传统医书中治疟的方子浩如烟海(单是《肘后备急方》里就罗列40多条),究竟该从哪几个方子切入展开研究与验证呢?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即便后续锁定青蒿作为重点攻关方向,由于中国南北方的青蒿叶在青蒿素含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课题组前期采用北方青蒿叶开展的研究工作始终难达预期成效。倘若一开始筛选样本时就选用南方的青蒿叶,青蒿素的成功提取或许就能提前实现。一言以蔽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需“严丝合缝”,否则就可能与有效药物擦肩而过。
另一方面,就医药研究来讲,即便在实验室取得了成果,要想让其真正惠及大众,还离不开诸多其他制度的支撑与协同配合。以现代医药工业为例,随着有机合成化学领域的发展,现代医药工业在二战后突飞猛进,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却相对迟缓,发展也较为滞后。这种状况直接致使“523任务”中关于青蒿素的科研成果,没能迅速转化为临床可用药物。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前来考察我国的药品生产管理状况时发现,竟然没有一家制药厂能够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标准要求。这一现实困境硬生生地将青蒿素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时间推迟了长达5年之久。
再看专利制度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产权与专利制度对于我们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新鲜事物,这无疑又给新药走向市场设置了一道不小的障碍。好在当时正在研发的复方蒿甲醚项目,由于起步相对较晚,尚未对外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研发团队历经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成功取得专利,并由诺华公司负责生产制造,推向国际市场。“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现的青蒿素,在30年之后终于登上了世界舞台,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最后要强调的是,新药研发过程中,如何平衡“义”与“利”的问题始终无法回避。药品研发工作,往往要倾注难以估量的人力、物力,可成功率却不足10%。这就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新药的钻研,究竟该投入多少资源才合适?一旦研发取得成功,又该怎么给药品定价?这摆在每一位新药研发人员以及每一家制药企业面前,并且在现代社会,这一难题愈发凸显。回首往昔,早期的科学家们,在进行科研工作时不太计较经济回报,更多是将科研当作纯粹的爱好,而非营生手段。就像1820年,法国的两位化学家兼药剂师佩尔蒂埃与卡文图,凭借精妙的实验设计,成功提取出对疟疾疗效显著的奎宁活性成分。他们毅然“拒绝从他们的发现中获利,因此没有就奎宁的提取过程申请专利,而是公布了所有细节,以便更多的药剂师提取奎宁,拯救更多的疟疾患者”。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现代学术职业体系以及药品研发、营销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新药研发工作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成本与收益相互权衡的逻辑框架之中加以考量。值得庆幸的是,青蒿素的发现,得益于中国国家力量的鼎力相助,恰好绕开了这一复杂的道德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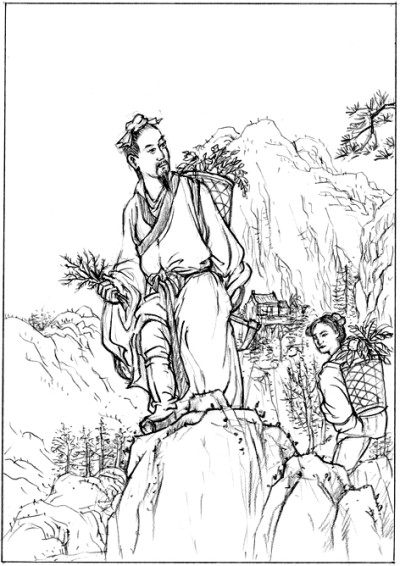
葛洪和道童在山中采药 任坚 绘
青蒿古方的现代崛起路
“双药”之一的青蒿素与1600多年前的《肘后备急方》有着奇妙的联系。但读罢此书,我们就知道不能简单将葛洪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与屠呦呦所发现的青蒿素建立直接的联系。事实上,其中的复杂性超乎我们的想象,也促使我们思考传统医药知识与经验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问题。
确定其中的有效成分并进行提取,乃至能够人工合成,这应该是多数中草药在现代社会仍能发挥功效的基本条件。当然这并非易事,需要上述种种条件才有可能达成。早在18世纪初,随着金鸡纳霜在欧洲的普遍使用,有人开始猜想各种草药中是否含有某些“活性成分”,对此是否可以加以纯化,如此治疗效果应该更佳。到1820年,人们确知奎宁即是金鸡纳霜中治疗疟疾的活性成分,但仍不知晓奎宁的理化性质。后来的科学家虽然研究出奎宁中各种原子的占比,但对原子之间如何相互连接组成分子结构还是一无所知。真正探知奎宁的分子结构并人工合成,这是二战之后的事了。
在我国,对抗疟药物活性成分的探寻并非直到“523任务”才起步。遥想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奎宁资源极度匮乏,在这一艰难处境下,中国现代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昌绍,毅然带领科研团队踏上探索之路,力求“从传统和民间医药中找到有效的疗法或药物”。他们将目光聚焦于常山,通过不懈努力,成功提取出“常山碱”,这一化学物质对疟原虫有着颇为强劲的抑制功效。
反观青蒿,虽说葛洪早早记录下这条方子,可在悠悠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它却近乎被世人遗忘。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就敏锐察觉到,自东晋以后,这一药方便极少现身于本草医籍之中。不过,李时珍也留意到,民间仍有不少人沿用这个方子,只是用药方式繁杂多样,疗效也参差不齐、难以稳定。而且,历代医师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青蒿一握”,对后半句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却常常视而不见。要知道,这里的“渍”意为“浸”,有别于中药惯常使用的煎汤、熬药、制丸等炮制之法。后来我们才明白,倘若经过蒸煮工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青蒿素便会大量分解,药效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诸多奥秘的揭晓,都有待屠呦呦那一瞬间的灵感闪现。“当年(1971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自此,“523任务”才最终以发现青蒿素而收官。
尽管特效药在手,但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疟原虫这种低等微生物基于快速繁衍和随机变异的基因分布多样性的优势,还在不断演化以适应环境,由此产生“耐药性”问题。迄今为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就有5次颁给了与疟疾治疗相关的研究,正说明疟原虫不会“坐以待毙”。看起来,这些微生物始终要与人类共存,对抗疟疾是一场“持久战”。这警示着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对抗疟疾只是一个缩影,守护健康、攻克疾病之路漫漫,唯有携手奋进,方能砥砺前行。
本文图片均选自《双药记》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2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