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经典漫步】
作者:梁衡(散文家,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文章的思想内容靠头脑指挥,而语言的运用则类似肌肉记忆,当你的笔在纸上滑行时,那字句是自动流出来的。如场上的运动员,攻防策略要动脑子,而反应的一刹那则靠肌肉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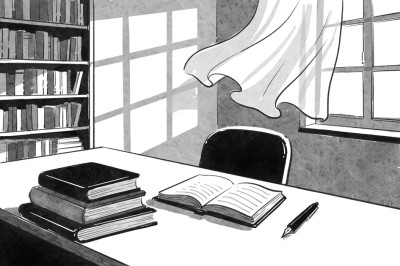
插图:周艺珣
我永远记得,中学语文课上老师讲过一个典故,说韩愈每为文时都要找出司马迁的一篇文章重读一遍,要借一口“气”。可见文章也是有基因的,可“遗传”。文学创作涉及语言的发展、积累。前人在文章中创造出经典的句子,我们在阅读时会吸收贮存,写作时,与它们有关的新句就会不假思索地跳到纸上。这种奥妙,只有写作者才能说清。
在我看来,语言的“肌肉记忆”可以分为深、浅两个层次。浅层的是形式上的句式记忆。有各种句子形式,三字句、四字句、五七言古诗句、词体长短句,以及古文或白话文中的句子,等等。有的句型已经定格为“公式”,常被后人模仿。如诸葛亮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深层的要复杂一点,是由意境勾起的句意记忆。作者根据脑子里一点幽远的记忆创作出当下的一个新句。原句与新句之间并无形式上的相似,却有语意的传承与关联。正如我们听歌时,突然觉得有几处旋律耳熟,那是作曲者吸收了别的曲子的元素。
不管是句式还是句意,这种记忆大多来自读过的经典作品,因为这些表达本身近乎完美,流传甚广,读者很容易接受。由此创作出的新句,让人有一种曲径通幽或他乡遇故知之感。
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的许多文句便源于这种“肌肉记忆”。
句式上的“肌肉记忆”是借来一个框,把新内容往里装。如《跨越百年的美丽》中写居里夫人:
她一生共得了十项奖金、十六种奖章、一百零七个名誉头衔,特别是两次获诺贝尔奖。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奖金赠给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奖章给六岁的小女儿去当玩具。上帝给的美形她都不为所累,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凭谁论短长,漫将浮名,换了精修细研。
这一段最末一句的总括、收拢,是借了柳永词的句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大约在初中时,我读到了元曲大家关汉卿的名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以后凡要表达激烈一点的语气,我就会想起这种句式。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的悲愤:
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又如在《二死其身的彭德怀》中,写到彭德怀一生转战的危险与艰难:
彭德怀行伍出身,自平江起义,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与死神擦边更是千回百次。井冈山失守,“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未死;长征始发,彭殿后,血染湘江,八万红军,死伤五万,未死;抗日,鬼子“扫荡”,围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彭奋力突围,未死;转战陕北,彭身为一线指挥,以两万兵敌胡宗南二十八万,几临险境,未死;朝鲜战争,敌机空袭,大火吞噬志愿军指挥部,参谋毛岸英等遇难,彭未死。
这段话一口气说完,类似曲艺中的“贯口”效果,句式源自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一个句子中包含18个分句,连用18个“死”字。
句意上的“肌肉记忆”,是只用其意,凭借记忆中某个句子的意境来构思新句。写作时头脑里忽然飘过一片云,落在纸上却成雨。在形式上已看不出原句的样子,但暗里仍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更需要灵感。
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夏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按绘画的观点,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
先把抽象的夏天转化成一种具体的颜色,然后从颜色上引申出感情,细细剖析——灵感来源于几十年前我读过的一位日本作家写的散文《月夜的美感》(夏丏尊译)。作者先将月亮设定为青色,再从青延展开来,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章。
《何处是乡愁》中有这一段:
村子成了空壳村,新盖的小学都没有了学生。空空新教室,来回燕穿梭。村庄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了笑声。
其中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影子。
《一个永恒的范仲淹》的结尾是这样的:
上车出城。路边闪过两个高大的石牌楼,突兀兀地在寒风中寂寞。人说这是当年衡王府的旧址,多么威风的皇族,现在只剩下这路边的牌楼和山上的寿字。遥望云门,雾霭中翠柏披拂,奇峰傲立。在山上刻字的人终究留不住,留下的是这默默无言的山;把门楼修得很高的人还是存不住,长存的是那些曾用生命去掮动历史车轮的人。
当时,我的脑子里一下跳出诗人臧克家写鲁迅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便遥借其意。
至于《乱世中的美神》的结尾“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有了答案,可是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的寻寻觅觅的美神”,则是借了范仲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语意。
以上几处在句式上与原句没有相似处,但在句意上是相通的。这是一种更深层的语言“肌肉记忆”。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靠这种深层记忆“翻新”出一个个鲜活的句子。
然而,很多时候句式与句意并不能截然分开,常常是既用其形又用其意,可谓混合记忆。就像打拳、跳舞、书法等,既有程式化的套路,又有临时应变的创新。
如《泥墙小院记》中的这一段:
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当日化软的冻土,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地亲吻冰凉的墙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犬牙龇咧的土坷垃,竟也一个一个地重新咬合在一起。我大奇,谁道人生不由己,门口斜墙尚能直!
最后一句源自苏轼的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文中逆境求生的心理与苏轼是相通的。
语言的“肌肉记忆”的形成,大部分靠读书,尤其是读经典文章,但也有不少是源于生活中的偶然相遇、随时抓取。
如《追寻那遥远的美丽》一文写王洛宾创作了那首名曲:
王洛宾真不愧为音乐大师,对于天地间和人心深处的美丽,“大师撮其神,一曲皆留住”。他偶至一个遥远的地方轻轻哼出一首歌,一下子就幻化成一个叫我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光环,美似穹庐,直到永远。
“大师撮其神,一曲皆留住”是从一幅画上得来的。何香凝老人画了一幅画,陈毅元帅在上面题了一首诗,首句是:“大师撮其神,一纸皆留住。”这里改“纸”为“曲”。
我有一篇写山西在“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的新闻稿,标题为《东一株西一株,积木成林 今一棵明一棵,坚持有益 山西“四旁”树木已占全省木材总蓄积量四分之一》。这个标题来源于早几年我还未当记者时听人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位画家画一赶路人,正挟一把雨伞急急行走在柳树林中。画家请诗人题画。诗人题道:“前边一株杨柳,后边一株杨柳。”画家说,废话!诗人接着题:“左边一棵杨柳,右边一棵杨柳。”画家说,你这臭诗真糟蹋了我的画。诗人说,别急。他接着写下“任他柳丝千万条,难将游人系”,顿然满纸生辉。这叫“逆挽法”。今天,它被我移来作新闻稿的标题。又如,一次给记者讲课,稿子里有一句“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这是由一个采购员谈采购工作时的一句话化用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每一篇评论都要有一个真靶子》,标题源自电视剧《亮剑》中的一句台词“每一个将军都要有一个假想敌”……
正如我们每天坚持锻炼才能维持肌肉量,语言的“肌肉记忆”也要靠长期的多读多背,多听多记,如蜂采蜜,聚沙成塔。读时要有时刻准备接收的头脑,目光一扫,好句、名句便收心底。写时随时接通“肌肉记忆”,旧句与新景就擦出火花。有一句话,“处处留心皆学问”,其实无论读书还是与人交流,处处留心皆好句,它们都可充实到自己的文章里。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出的文章就会更上一层楼。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8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