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邱瑾(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作家像简·奥斯汀这样,能激起如此广泛持久的热爱,也鲜有作家像她这样,引发如此纷繁复杂的误解。
今年是奥斯汀诞辰250周年。1775年12月16日,奥斯汀出生于英国汉普郡史蒂文顿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她一生未出过国,未结婚生子,留下六部小说代表作,41岁时离世。每一个去温彻斯特——奥斯汀的逝世地——文学“朝圣”的书迷,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目标。在那座安葬着多位历代权贵的教堂里,唯有奥斯汀的碑前常年盛放着鲜花。
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傲慢与偏见》时,禁不住要问:对于我们来说,奥斯汀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她,纪念她?

简·奥斯汀 资料图片
Ⅰ 被误解的艺术家
在大众想象中,奥斯汀常常化身为一位隐居田园乡间的优雅淑女,一个“平生无大事”的文学天才。这一形象源自其侄子奥斯汀-利所撰的《回忆录》(1870)。在这本首部奥斯汀传记中,她被塑造为一位感人的“简姑妈”——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家务之余用写作自娱自乐。
关于她的作品,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她只会写爱情和婚姻,是“霸总小说”的鼻祖、“逃避文学”的大师。另一个误解是,她只写家长里短、人情世故,题材狭窄,故事琐碎。由于奥斯汀自称作品为“二寸牙雕”,让很多人误以为她的艺术特色只在精细,然而视野不够宽宏,内涵不够深厚。
奥斯汀生活在英国摄政时代。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她有意避开重大时事——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而选择以方寸小村为笔下天地,从三四人家写世态俗情。正如同时代的大作家司各特所言,这恰恰体现了她的原创性和独特性。
她的小说的确围绕婚恋展开,可这与其说是个人偏好,不如视为市场所需。十八、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女性被排除在工业世界之外,但出版业的发展使写作成为她们的新兴职业。小说市场既为女性作者带来机遇,也使她们面临身份焦虑与创作局限——她们大多只能聚焦道德教化或婚恋题材。奥斯汀看似写婚恋,实际上恋爱细节她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反而绘声绘色地展现聚会互访等社交活动。她始终把婚恋问题放到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将其与社群、阶级话题紧密关联。
而将奥斯汀视为“温柔的姑妈”和“无心插柳的天才”,则是对于作家本人最大的误解。在其早期作品、书信及后来的各种传记、研究中,有诸多证据显示,她的性格绝不只有温顺的一面。她从少女时代就有志写作,反复修改打磨初稿,多次托父兄投稿、谋划出版,甚至亲自出面与出版商就版权问题进行交涉。她的作品问世过程充满了坎坷,在世亦谈不上名利双收,但她执着于出书,还对家人表示希望自己能挣得更多。真实的奥斯汀一如她的作品,具有多维的构成和丰富的层次:外表温婉得体,内里不失锋芒,而底色是属于艺术家的坚毅与“雄心”。
Ⅱ 奥斯汀的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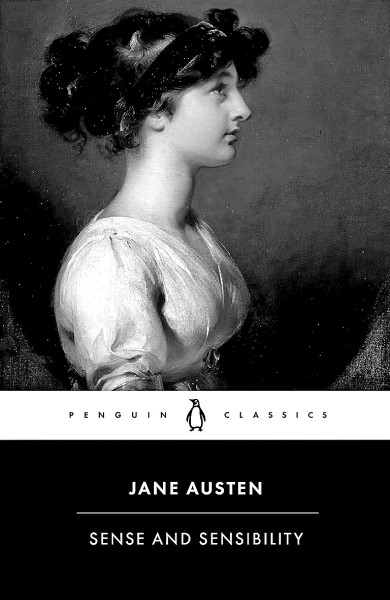
《理智与情感》书封 资料图片
为什么奥斯汀会如此受欢迎?她的作品魅力何在?每一位新读者都不免发问,而每一个老“简迷”都会争相去解答。但接下来,新读者会更加困惑——不同时代的读者赋予她截然不同的标签,不同派别的批评家都会将“奥斯汀”拉入自己的阵营。
她是保守派的砥柱,也是进步分子的同盟;她是严肃端庄的卫道士,也是幽默诙谐的喜剧家;她是新古典主义的继承者,也是浪漫主义的号角手,更是现实主义的代言人;她是尊崇规则的风雅之士,也是颠覆规则的时代先锋。可以说她的各方拥趸都没有错,也可以说大家都误解了她——与其说是我们在解读奥斯汀,不如说每个人都从奥斯汀的密码中破译出了自己。
其实,奥斯汀最核心的魅力就蕴藏在上述的二元对立中,她却能以圆融通透的人生哲学、细腻高超的艺术手法超越各种对立面并将之融合,简而言之,就是达到一种“矛盾与和谐”。
在她的作品中,既有沉稳老练的处世之道,也有灵动鲜活的赤子之心;既有对他人眼光的在意,也有对主体身份的坚持;既有对规范的遵从,也有对真善的求索;既有审慎的理性,也有炽热的深情。
这种复杂性从她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便可看出。她笔下有不少活泼的女主人公:《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热情奔放;《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曾俨然一个假小子;《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机敏伶俐,为探望生病的姐姐,不顾“形象”奔跑于山野。她们生命力旺盛,本能地抗拒被社会规训。然而,作者的高明在于她并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物固化扁平。随着故事发展,这些活力女孩都渐渐学会了自己的功课:要么用理智平衡情感,要么摆脱胡思乱想,要么跳出自我中心。而其他貌似更为“文静”的女主角,在其温柔的表象之下都蕴藏着强大的内核。《理智与情感》中看似理智的埃利诺克制着内心汹涌的情感,万箭穿心仍勇敢承担守护家人的重任;《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抵御“大众情人”亨利的追求,拒绝“恩人”托马斯爵士的指令,用含蓄静默的方式坚定地对抗父权。而爱玛——这位奥斯汀在《爱玛》首页就描述为“仿佛人生几大福分让她占全”、同时也是奥斯汀声称“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特别喜欢的女主角”,在发现自我蒙蔽的真相时那番含泪自省,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哪怕你拥有世俗眼中的“顶配”人生,仍有需要克服的认知盲点,也要经历心灵的黑暗。而经过灵魂跋涉成为理性主体,是奥斯汀的女主角们的必经路程。她们轻易不动心,一旦爱上,往往爱得专一而深沉,炽热而浓烈。这点在《劝导》中的安妮——奥斯汀作品中最冷静成熟、被认为最像她自己的女主角身上体现尤甚。这种动与静、柔与刚、明与暗、冰与火的融合交织,使得人物形象极富内涵,极具深度,极有张力。
这份张力也体现于她笔下的爱情与婚姻。为什么《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故事会如此打动人心?如果只是又一个俗套的“霸总爱上我”,怎会激起一代代读者的想象、向往和共鸣?正因为,这个故事表面说恋爱,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成为“我”,又怎么联结“我”和“他/她”,而这恰恰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些课题。即使伊丽莎白没有遇到达西,她也不会成为嫁给柯林斯的夏洛特;即使达西没有爱上伊丽莎白,他也不会去倾慕工于算计的卡罗琳或弱不禁风的贵族小姐德波尔。伊丽莎白和达西表面上阶层不同、性格各异,但在坚决捍卫自我原则这点上却非常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与所处环境进行抗争的人。若没有相互联结,也许他们本性不移但终会囿于褊狭的自我;而相遇后,他们因对方的映照而学会了觉察和反思,摒弃了在“自我”背后潜伏着的傲慢与偏见,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个性成熟和相互理解。奥斯汀通过这个故事示范了爱情的本质和最高境界。其他作品中,她也同样以婚恋为道场,调适、糅合各种对立的要素——最凸显的就是经济利益与情感欲望、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环境的矛盾。真正的“花好月圆”象征着冲突之上更高层面的平衡、和解与更新。个体通过亲密关系,不但实现自身的成长进化,也以更协调的方式适应或改进现实环境,体现矛盾与和谐的智慧。
奥斯汀作品中透露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同样如此。在外部世界纷繁芜杂之时,她转而描写宁静的乡村生活,用安宁反射嘈杂,用规则映衬动荡。她讨论的是个人如何在既定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又如何通过人际交往互动隐性地构建社会现实,从而参与社会形态的塑造。她有意选择的艺术手法,是用中产阶级的题材、普通日常的细节,去再现当时不同阶级的角力和融合;用“反讽”和自由间接引语等特殊技巧,去提供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阐释空间;用看似“微小”的规模、精准简练的笔触,去勾画一幅蕴含着更大视野和格局的艺术图卷。通过“小”与“大”的对立统一,她挑战和重构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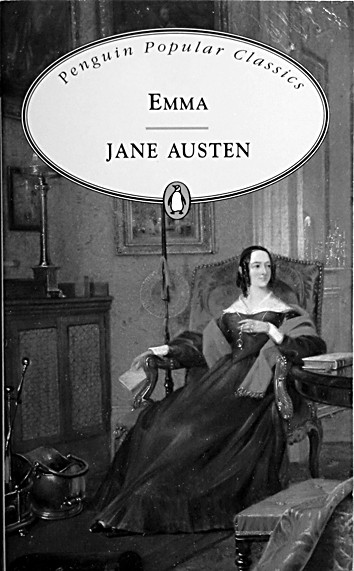
《爱玛》书封 资料图片
Ⅲ 成为“简·奥斯汀”

范尼·伯尼 资料图片
或许正是由于奥斯汀作品的复杂和丰富,她的影响也广泛而持久,矛盾而多重。
首先,她给文学史制造了“麻烦”,却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史。在她之前,十八世纪的笛福、菲尔丁等人以冒险主题和社会批判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在她同时代,司各特的浪漫英雄小说风靡一时,市场上流行的则多是言情、哥特等通俗小说;在她之后,“现实主义小说”的概念才逐渐被提出。她虽难以被完全归入任一流派,却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见证并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兴起与转型。1923年,时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查普曼将奥斯汀作品集编辑出版。编者像研究古典诗人和剧作家一样去对待一位小说家,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可以说奥斯汀跻身经典与小说的学术化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她的“经典化”又与商业一路交织。最早帮助她扩大了影响的《爱玛》的评论,实际上是司各特应出版商之邀为提高销量而写的。《回忆录》引发首次奥斯汀热潮后,一边是文学史、教材将奥斯汀收编其中,一边是奥斯汀作品更豪华的版本、衍生品相继问世,以至于亨利·詹姆斯发出著名的抱怨:“一大群出版商、编辑、插画家以及给杂志制造愉快闲聊话题的人发现了他们亲爱的、我们亲爱的、人人亲爱的简,可以无休止地为其谋利。”
作为女性作家,奥斯汀理应归入女性文学传统,但早期评论多将她与莎士比亚、塞缪尔·理查逊相提并论,很少关联其他女作家,或许也是因为她难于归类,使她同其他文学姊妹貌似迥异。夏洛蒂·勃朗特曾批评奥斯汀“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不料两百年后,观众眼中奥斯汀影视改编的主角恰似“勃朗特小说人物”。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奥斯汀与同代或后起的女作家如埃奇沃思、范尼·伯尼、乔治·艾略特等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女作家——如朱莉亚·卡瓦纳、伍尔芙等,从奥斯汀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与主流评价相悖的她,一直试图去解构“简姑妈”形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学界开始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奥斯汀。学者巴特勒突破当时形式研究局限,将奥斯汀与历史社会话题相关联,称其为托利派女性主义,学者柯卡姆认为其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同属启蒙女性主义者,激进女性主义者赞扬她以隐蔽的方式就性别议题表达颠覆性观点,亦有激进女性主义者反过来批判她保守。可见,围绕奥斯汀的解读与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更耐人寻味的是诸多男性文人对奥斯汀的反应。“简迷”(Janeite)这一称呼据说源于批评家乔治·森茨伯里——1894年他在为一版《傲慢与偏见》作序时以此自称。一战后,“简迷”的代表是以查普曼为首的一群文人雅士,即伍尔芙口中那“25个住在伦敦的老年绅士,容不得对她天才的轻视”。这些掌握批评话语权的绅士学者,对“简姑妈”满怀深切复杂的文化乡愁,视其为文学避难所与精神解药。今天的“奥斯汀”依然肩负着民族遗产的重任——皇家邮政为其发行纪念邮票,央行将她的肖像印于新版10英镑钞票上(取代达尔文),她也是目前除女王外唯一登上英国货币的女性。今年恰逢奥斯汀诞辰250周年,英国多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仿佛只要“奥斯汀”还在,一个想象中的“英国”便还在。
不过,也并非人人都爱奥斯汀。比如两位美国知名反对者——爱默生称其“缺乏创新,只关心能否结婚”;马克·吐温说读其小说“如酒吧老板入天国”。文学评论家莱·特里林将这解读为“男子对一个妇女居于兴趣和权力中心的社会所产生的本能的反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福斯特等人对她的感受则更为复杂。詹姆斯起初盛赞奥斯汀的艺术造诣,而后却说她缺乏深度。福斯特原是十足的“简迷”,后来却诟病其“怀旧”特质。其实詹福二人都可视为奥斯汀的文学后继者。学者图特指出,这反映出一些男作家在继承女性文学传统时的身份焦虑。当今众多作者(不论男女)都坦言曾从奥斯汀作品汲取灵感与技巧,如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称其代表作《赎罪》为“简·奥斯汀小说”,被誉为“当代推理小说女王”的P.D.詹姆斯将《爱玛》视为侦探小说的典范……这证明了奥斯汀的文学遗产是人类的财富,而不必打上刻板的性别标签。
当然,爱默生们的反感另有原因——当时美国是新生国家,正努力在政治、文化上摆脱英国影响,而奥斯汀被赋予的“英国性”与之冲突。有意思的是,作为美国文学艺术学会首任主席,同样致力于开创美国文学传统的威廉·豪威尔斯却大力宣扬奥斯汀的“现代性”“独创性”和“独立精神”,认为她在英国小说中独树一帜,精神上更接近美国小说,把健康淳朴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留给了美国人。同一个奥斯汀,既可象征逝去的家园而被怀念,也可因“异己”标签而招致批判,还能因独特性被纳入美国建构自身文化的话语中。
如今,“简迷”们能以前所未有的便利感受奥斯汀无处不在的影响。他们可以上午读孙致礼教授的译本,中午观看传记影片《成为简·奥斯汀》,下午去“彭伯里共和国”(美国“简迷”创立的论坛)和异国网友聊天,晚间到“乐乎”上发表相关同人创作。他们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既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今天,奥斯汀之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她、纪念她?
在无数可能的答案中,笔者最想说的是:因为她鼓励我们去勇敢地追求幸福生活。她让我们认识到,幸福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灰姑娘的白日梦,而是基于现实的平衡把握,是现代人要力修的功课。她让我们对生活、对他人、对自己都保持更加清醒的观照,同时也永葆希望和热情。她让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读者,以多元共生的方式去感受快乐、确立身份、创建联结、寻求共鸣。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奥斯汀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她笔下的人物和历史上饱受桎梏的中国女性不无共鸣,也能给当代获得解放和经济独立后的新时代女性带来启发,即如何在社会、职业、婚姻、家庭关系面临困境时找到解决之道。她小说中有姐妹的情谊,有亲友的关怀,有社群纽带,个体和环境虽有矛盾但终能归于和谐,这和中国文化对于“关系”的重视彼此呼应。她作品中反映的婚恋观和人生观,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和谐”亦有相通之处。她的文字能增加我们的洞察力,明确个体于社会中的定位,从矛盾中探索新的和谐与平衡。

乔治·艾略特 资料图片

玛利亚·埃奇沃思 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