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田峰(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不仅关注边疆地区作为“自在的空间”在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且通过边疆内部的运行机制探讨边疆与中原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点。这种思路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正因为边疆的存在,中原才是有意义的。文学也是如此,就唐诗而言,以“边缘”形式存在的西域与岭南,对唐代诗歌艺术有了极大的推进。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对唐代文学进行重新认识,从“异域”角度看唐代诗歌的新变,是一个新的视角,是对以往从诗歌内部研究唐诗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深化对唐代文学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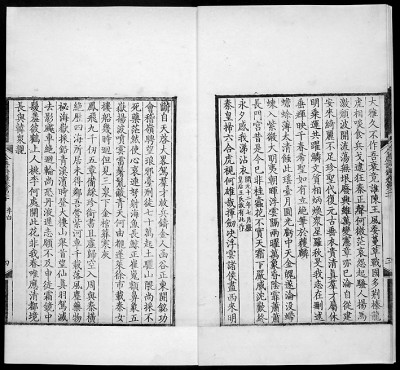
清代徐倬编《御定全唐诗录》 资料图片
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主要包括巴蜀、荆湘以及吴越等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和岭南为主要区域的“边疆文化圈”。初盛唐诗歌的演进,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外部的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新变的关键,地域因素排在首位,尤其“异域”(即边疆文化圈)因素对诗歌的冲击值得注意。初唐诗坛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带,以奉和、应制、酬唱、赠答等诗歌为主,较南朝文学发展变化不大。“异域”进入初唐诗坛,诗歌在悄然发生变化。唐代典型的“异域”,一是西域,一是岭南,有关西域的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有关岭南的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初唐时期长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宫廷为中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题材狭窄,视野有限,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水平。《沧浪诗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是从题材角度对唐诗进行的整体评价,但若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看,征戍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有关西域的边塞诗,迁谪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贬谪岭南的诗歌。另外,贬谪行旅诗、贬谪离别诗中,其中有关岭南的因为距离遥远和情感体验最为强烈,因而富有冲击力;征戍行旅诗、出塞离别诗中有关西域的则将战争的氛围与疆域的拓展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严羽所说的唐人好诗,皆与西域与岭南关系紧密,这两个地域的诗歌在初盛唐诗坛振聋发聩,使诗歌境界大开。
西域与岭南的诗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模式,前者承征戍文学而来,疆土开拓与个人建功立业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盛唐边塞诗雄浑壮阔的特点。宋代之前,中原向外发展主要在西北方向,因而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开始,想象的西域世界与现实的西域交相辉映,已形成了昆仑、流沙等重要意象。随着汉代对西域的开拓,游仙诗与乐府旧体中逐渐有了西域意象。唐之前,西域意象在诗歌领域极为有限,不具有典型性,但唐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使楼兰、交河、轮台、北庭等典型的西域意象有了新变,对边塞诗境界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马蹄经月窟,剑术指楼兰,地出北庭尽,城临西海寒。”皆呈现出博大雄厚的气势,与盛唐精神一致。同时也凝结成了一些新的西域意象,天山便是其中之一。如王维:“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岑参:“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这些诗歌中的天山衬托出了一种疆域辽阔、雄壮苍茫的意境。唐代诗人中只有来济、骆宾王、岑参、张宣明、萧沼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去过西域,除了岑参留下大量有关西域的边塞诗作外,其他诗人所存有关西域的边塞诗极为有限。岑参前后两次到达西域,对西域世界的感知最为具体、深入,他的边塞诗之奇,在整个唐代无出其右。《唐音癸签》认为其诗“尚巧主景”。这种“主景”自然涉及他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王昌龄、王维等绝不相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西域的书写。其他边塞诗人所写多为朔风、蓬草、胡马等最常见的物象,但岑参的诗歌进一步具体化,如《火山云歌送别》《经火山》《碛中作》《日没贺延碛作》等诗都落到实处,将边塞诗之“异”更为直观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荒凉广袤的雪山大漠与开疆拓土的热情也形成了一种反差审美,造就了“雄瑰”的诗境。如写火山:“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写热海:“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写银山碛西馆:“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皆给人以“奇伟”之感。正因为对西域的书写,岑参的边塞诗气象声色兼备,为古今边塞诗第一人。
与西域相比,岭南完全呈现出相反的情景,因为是贬谪,“荒蛮”的景象与个体人生的低潮纠结在一起,诗歌具有低回宛转的特点,情感真挚而深沉。初唐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开启了岭南诗歌的新纪元,这些诗歌情景交融,对打破沉寂的初唐诗坛功不可没,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其一:“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这是一首成熟的五律,首联写离别中原时的踌躇,颔联魂、泪相对,南翥鸟与北枝花相对,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反差,颈联看似写景实为写情,尾联直抒胸臆。这首诗“气格声色兼备”(许学夷《诗源辨体》),在初唐诗坛别有风味。这样的贬谪行旅诗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沈佺期的《入鬼门关》《初达[~符号~]州》《度安海入龙编》,宋之问的《早发韶州》《早发大庾岭》《鬼门关》《发滕州》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诗中作者常将岭南看作是“魑魅”之乡,情感指向绝域、极边;从空间看,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二者之间的对立,陌生的空间对作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对诗歌来说又是极大的幸事。北斗对南风、北斗对南荒,江北对岭南、南溟对北户、北极对南溟,京华对边地,不仅有南北空间的对立,而且也有新的物象如桄榔、薜荔、卢橘、杨梅、含沙、女草、鳌、鲸、蛟螭、瘴疠入诗,一方面使诗歌“陌生化”,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物象成为新的诗歌意象,恰是对初唐诗坛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中心”书写的回应。这些诗歌在情感上不再是无病呻吟,而是句句落到实处,掷地有声。这种空间的对立,对对仗精工的律句的形成无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翻检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在岭南的诗歌创作,最直观的印象便是状物写景愈加精工,近似排律的诗歌逐渐增多。这些贬谪岭南的诗人,情感绝望,对新事物多怀鄙夷之情,但是有意无意中也使岭南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初唐以后贬谪岭南的文人大量增加,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牛僧孺、李德裕、李绅等,宋代文人如姚铉、寇准、苏轼、苏辙、黄庭坚、范祖禹、秦观等都曾贬谪岭南,而且多数文人都有大量诗作传世,中唐以后对岭南的审美也由排斥到逐渐接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审美文化。
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与情合,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因而唐代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在内容、艺术形式、境界等方面都对唐诗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域代表疆域的拓展,岭南则代表荒蛮之地,皆为“异域”,亢奋与落寞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遥相呼应,两个地域都与政治前途密切相连,皆处“边缘”,却无形中观照“中心”,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是互相塑造的共生体。这种书写对唐代文学乃至后世的文学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7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