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葛水平(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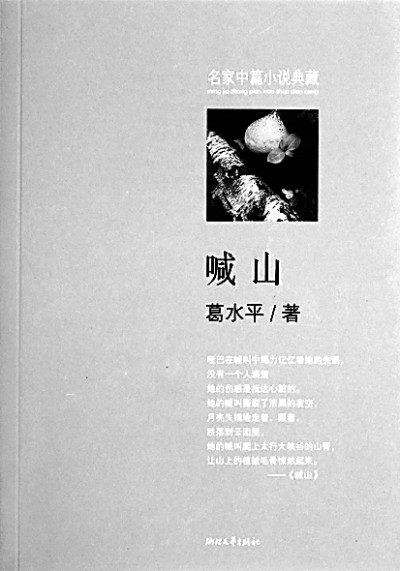
一
春天,一场大雪阻挡了回城的路。我和表弟文军站在他家羊圈的篱笆墙前,满圈的绵羊,因为我们的到来,眼睛直戳戳盯过来。它们的样子让我惊奇,此刻,假如有一只羊张嘴说话,一圈羊的叫声就会此起彼伏,那情景十分迷人。
表弟是我们这个家族唯一没有离开老家的人,不离开是因为离开老家,羊群没有更好的落脚处。
表弟和羊相伴经年,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对方的气息与温度,他们之间有一种局外人不理解的情愫,有友谊有爱有平等也有相互的感恩,甚至更多。表弟尽其知识储备,给他放过的每一只羊都取了名字。公绵羊在老家的方言中叫“圪羝”,公山羊在方言中叫“骚胡”。“圪羝”类的取了“喜孩”“必土”等,“骚胡”类的取了“喜民”“山汉”等,母羊则一律被亲切喊“彩彩”。这些羊名字是表弟一生中创作出的最经典的文学作品。有一阵子,我的小说中人物名字来处就是表弟嘴里的羊名字。那些名字,没有一点羊态,每一张面容上都涂了一层柔丽,一副明眸皓齿的样子。文字中的他们,一颦一笑,一蹙眉一眨眼,又都散发出一种令人惊叹的美仪“羊”态。
南宋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撰写诗《咏羊》言志:“出都不失成君义,跪乳能知报母情。”在汉字中,以羊为部首的或含有羊字的汉字有204个,除了“差”以外,“祥”“善”“美”等203个都是褒义字或中性字,可见人们对羊是寄予美好向往的。
老家人说话土,表弟一口土话。从前外出读书人回乡说普通话要被村里人嘲讽,“走了几天,人就疙汰了”(意为“忘本,故意拉开和乡村人距离,显出格格不入的样子”)。老家的土话有意思,叫山丘“疙梁”,叫背心“疙拉拉”,喊太阳“饵篓”,拍胸腔是拍“疙廊”。
太行山逶迤,山路崎岖,老祖宗世代肩挑背扛种地打粮过日子,可日子过着,变化就来了。只要有一个人走出去,那些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灯火的老家人不免心跳加速:离开意味着再也回不来了。
“人挪活,树挪死。”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句话。
表弟不舍得离开老家,站在老家的山疙梁上,穿着红色的“疙拉拉”,看着“饵篓”升起落下,“疙廊”里装满了不舍得离开老家的泪水。
眼看着道路延伸了希望,也带走了一切,没想到的是羊决定了表弟的命运。

葛水平乡野村趣画 资料图片
二
放羊不杀羊,是表弟做羊倌的原则。他总说和羊感情缠绵多年,一直都怀念和羊一起成长的岁月,似乎在成长过程中也吃透了羊的性格。可生活中发生了两件打动人心的事,表弟一个人站在山坡上还哭了两回,最后痛下决心不离开老家。
头年的母羊被山外的羊倌买走了。后来,他出山去找人说私事,途中在一个村庄街道旁的一家面馆吃碗面。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而黄昏是一天里最宁静的时刻,在没有食客到来的房间里,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去。表弟常年在山上吼羊,粗喉咙大嗓门,表弟带着响进门时,连陈旧的漆皮和胶合板家具都被“惊醒”了。遇见同样想吃一碗面的乡民,老家人说话没有繁文缛节,一边吃面,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年景。一个说,一年时间短得比小孩的尿还短,人一辈子都在折腾福分。一个又说,背阴坡上的寺庙今年秋口上塌出了一个疙隆,有人偷走了庙柱下的柱础,离乡人不疼爱自己的老家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没有多少悲伤,而是羡慕村庄里远走的人。寻找更安乐、更舒适的生存状态,也许是人一辈子的正经事。
门外街道上有一群羊走过,一只羊停在了饭店门口望着门里“唛唛”叫,一声紧跟一声。两个吃面人盯着门口的撵羊人奇怪,门槛上咋探出一只羊脑袋?文军一下就看见倚门叫着的羊,正是他转手卖出去的“彩彩”。文军呲着豁牙笑,抚摸着羊脑袋想哭,羊“唛唛”叫。“唛唛”是羊唯一的语言。
文军说:“还听得出我的声音来,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记挂过你呀。”“彩彩”被赶羊人撵走了。
原主人不给羊好命,羊还记挂着原来的主人。
养羊人有自己的地界,山下沟为界,羊群在自己的地界内吃草。某一天,突然从对面的山头上跌跌撞撞走下来一只羊,走到文军放羊的山坡下,没入草丛不见了。表弟从山头慢条斯理走近看,看见一只羊卧在草丛中生育,母羊舔着湿漉漉的小羊羔,看见表弟走来,母羊叫着,站起来丢下小羊跌跌撞撞走了。这是自己去年卖了的“彩彩”呀!
母羊感恩从前的主人,丢下一只小羊羔子走了。
表弟在黄土疙梁上难过了一阵子,羊不是宠物。宠物与人相似,争宠。羊只知道羊倌放养它在疙梁上,土地接纳了母亲般的“饵篓”送来的阳光,一年四季,土地的呼吸,宛如母亲的呼吸,比山头更为辽阔,尽管土地似无声无息,然却恩泽生灵,给生灵爱。就像梭罗说的,有如山间的空气会喂养灵魂,启发灵性。
羊的行动,凭直觉爱人,不生仇恨。
表弟在疙梁上用手甩着泪蛋子,哭到最后想明白了,羊都知道恋主,自己为啥要离乡背井?
三
对老家的牵挂,也是对旧时过日子的牵挂,那里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新旧陈杂,轻重各异,如同儿时许下的诺言“不分离”,生活的剧情向前展开,谁也猜不透多变的世相。
在老家,我见过母羊和小羊分圈的情景。母羊要出山了,小羊如一个人的童年,还不知脚下深浅,要留在羊圈。表弟挥舞着羊鞭,一下两下,母羊开始往羊圈栅栏门方向走,小羊在鞭声中跌跌撞撞,找不到母亲,见任何一只羊从身边走过都认为是自己的亲娘“彩彩”,用羊角顶撞母羊的可爱劲儿,那一瞬间,生活的剧情向前展开。
母羊们在鞭声甩击中走向山腰,长长的羊群,荡起了黄尘。
又听表弟讲一只母羊死去,表弟用小羊的胞衣涂抹在其中一只母羊“彩彩”身体上,血水淋漓,小羊跌跌撞撞寻着娘的味道。
娘的味道,前所未有的疼痛,勾勒、构建并呈现老家之所以为老家的光亮属性。
娘的味道就是老家啊!
灶间烟火兴旺,日子才会兴旺。烟火气不灭,日子才能好过。
城市的方向一直是老家人富足的梦想地。那么土地呢?大面积的土地开始闲置,人总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会想到土地。
乡民说:我不想让土地闲着,土闲了长草;我也不想让我闲着,人闲了难受。
出门人成了外乡人。
世相多变,性格固执坚守是不是就是人的福气?
我在老家寻找乡俗俚语,老家话形象十足,没有规矩地乱开乱合的亲切感,成为我明亮或者幽暗的知识河道。
我坚信重返故乡是未来人的必然方向。看那二里三里高的疙梁上,晚阳挂在西天边,浮游的尘土托着一方酱紫,裹一身春风转身。
其实,作家的蜿蜒走势皆因为自己的命运和定力。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资使用,建立在自认是好的“过去”之上,用记忆中的经验寻找故事。对我而言,生命里如果出现一个心仪的朋友,那一定是在老家,老家人用“土话”满足了我继续生活的喜悦心情。
四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走到疙梁坡上,看见表弟躺在草皮上入睡,睡得很放肆,四仰八叉,“饵篓”在高处懒懒散散相拥,不亲近,也不躲闪,草皮上的鼾声此起彼伏。羊埋头吃草,鼾声逸出来的自在味道是整个乡村美好心灵的实录。一辈子没有睡过一张好床的表弟,在羊们的簇拥下睡得如此踏实。
想起童年时夏日的夜晚,院子里铺一领苇席,男人女人孩子们都坐在上面,月光明晃晃地当头照下来,等于给梦找一个栖身之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蛙鸣声弹着青玉米的叶子,明丽的月影朗照一切,白天出山的大人们把山外听来的事努力用农民文学家的口吻复述一遍,谁都怕上茅(厕所)误了精彩的一段。小孩子们不敢大声喊叫,怕一不留神碰落了玉米的香气、青草的香气。月影下老窑花纹繁复的窗栏板,一棵树宽的门扇,紫铜的门环,铁葫芦锁,他们看着看着,睡意来了,不等散场就睡过去了,被大人喊醒时骨软脑糊,恨不得睡死过去。
那样的睡眠,居住在城里的我再没有找到过。面对老家的从前和现在,我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我从老家人的故事中获得创作源泉,表弟和羊群守着自然秩序。在老家,人们对所有的生命都以兄弟相称,一辈子各安天命,各从其类,但关键时刻总有灵性呈现。
生活本是一大堆细枝末节,有的枝节在寒来暑往的转换中永久地风干了,像寻常的小情小调、小伤小悲;有的枝节却四季青葱,永驻我们的心间,比如守护老家的表弟和羊群。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感动的记忆。就我而言,感动过心灵的怎能忘怀,又焉能忘怀?纵然是一个小小的举动,或是一句温暖的话,或是一个会意的眼神,无一不是人类高尚心性的自然外露。我常常沉浸在对老家人事的回忆中,被那些曾经的感动永远地感动着,这无数美好的感动,像火种一样点燃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热忱和欲望。也正是有了这些人、这些事,我生活的天地才越发绚烂明媚。
我选择写手艺人、写乡村。相比时间,他们是有重量的,他们的故事透彻地穿越时间留存下来,他们的坚守也许让我能够看见乡村的远方。
土得掉渣的老家话有水土流转深远的遗传,紧张的生活和过多物质需求相比,老家话和老家人,暗含着某种幸福的从前。
当一个人常常被老家感动也常常能给老家人感动时,那无疑是一种人生最好的感觉。我尽力在找这样的感觉。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21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