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刘孝存(作家、文化学者,曾任北京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北京话,与北京建城史联系在一起,与北京的历史风云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历代的北京人联系在一起。从蓟燕语,到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到明、清北京话,及至当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多少腔调音韵的溪流汇成了北京语言的长河。

北京金中都公园内营城建都雕塑 资料图片
北京话源头——“蓟燕语”
北京话的源头,出自我国古代边邑“蓟丘”的“蓟燕语”。
我国古代,北京地区被称为“幽陵”。幽者,深远也;陵者,丘陵也。相传,帝尧时代在幽陵一带建“幽都”,顾名思义,它应该有边远城邑的意思。这种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叫作“史前时期”;人们的记事或交流,只能结绳、画图画或使用手势、口语。若是想将见闻、经验传给后人,就要利用歌谣、谚语和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说,一代一代传下去。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的封地,据考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但召公并没有当即移足燕地,而是参加了平息管蔡武庚之乱的战事。召公的原封地“召”,在今陕西岐山西南,当时的周人都城为镐京。召公未到封地,并不等于他不派部众前往燕地;众多的管家、吏役、兵将等,所操语言的语音应该属于“周语”(镐京语音)。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发掘的棺木中,出土了西周早期甲骨文残片,可认证当年蓟燕都城的纪事,承袭了刻在龟甲或牛骨上的殷周甲骨文。
燕国有纪年可考的时间,始于燕惠侯元年(公元前865年)。后来燕襄公将都城从易迁到蓟地都邑蓟城。据考,蓟丘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北京之西,被统称为西山,属于太行山余脉;其北军都山东延至山海关,为燕山山脉。
当年燕都蓟城人的口语,应该是融会了周语和蓟地土语(多民族混居地产生)的混合语;而文字,大概是钟鼎文(金文)或竹简文、木简文。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有二百多个“籀文”。据说这籀文,是周宣王时期名叫“史籀”的太史所撰。

周平王东迁,将王城设在成周城(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之东),史称“东周”。周平王及其部众讲说的镐京语,渐渐与成周语融会,形成了“雅言”。雅言,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周新王城与各方国沟通的通用语言。相传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鲁国人孔子,就是以雅言给来自各国的弟子授课的。
燕国是宗主周王之下的方国,自然需要在官场中推行雅言。但蓟燕方言依然是燕地的民间流行语。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1年),昭王在易水旁修建黄金台招贤纳士,所出的告示使用的应该是钟鼎文或石鼓文;前来应招的魏国人乐毅、齐国人邹衍、赵国人剧辛等,自会以雅言相通。
最早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燕春秋》,见于《墨子》;记述“荆轲刺秦王”的《燕丹子》,见于明代的《永乐大典》。
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并在官方文书中统一为“小篆”。秦都咸阳的咸阳话,上升为大秦帝国的官话。但由于秦朝的国运仅为十五年,短时间内将咸阳官话替代各郡县的官话有一定难度。若要覆盖民间言语,只能是一个泡影。
秦代燕地流行的依然是蓟燕方言。西汉杨雄撰有《方言》书,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并注明通行范围。其中,将冀州(河北)、并州(山西)及青州、兖州、徐州(三州为山东)一带的一种方言称为“幽燕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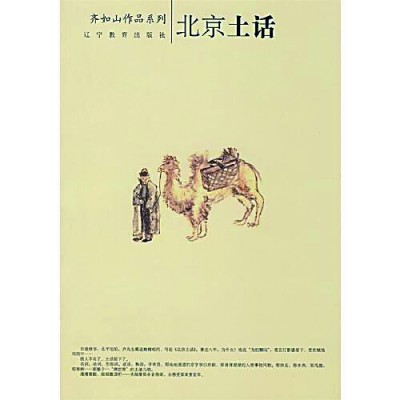
“幽州语”和“幽燕语”
大唐的幽州,是汉人与突厥人、靺鞨人、奚人、契丹人、室韦人等杂居的地方。语言学者以幽州为坐标,将唐代幽燕地区语言称为“幽州语”。
幽州语与大唐中原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和传承关系。“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他的诗集《幽忧子集》今存诗90余首。留下“推敲”典故的唐代大诗人贾岛,范阳人,有《长江集》10卷,留诗370首。陈子昂虽然不是幽州人,但他随军于幽州时留下的《登幽州台歌》却是千古流传。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在《北风行》中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之句。
经历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和沙驼人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之献,契丹族的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南京”。契丹是鲜卑人的一支,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得燕云十六州后,其领地内增添了大批汉人。其间,南京又曾改为燕京,幽都府改为析津府,幽都县改为宛平县。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联宋而灭辽。金完颜亮(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后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仿宋汴梁城规制,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原析津府改为大兴府,辖大兴、宛平等县。当时中都城居住多个民族,计有女真、汉、渤海、契丹、奚等。
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北京地区,同时亦有大量汉人被动或主动迁入原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金代,汉人被驱掠、迁徙到女真地区的为数很多。在这种不同民族混居、融会的历史背景之下,幽州语受阿尔泰语影响(女真语亦属阿尔泰语系),特别是在契丹语和女真语的影响下,“幽州语”演变成“幽燕语”。
金代科举,设“词赋科”,即取士为官,要有词赋的笔试,由此,中都的皇室、贵族、官员,包括汉族士子,多能诗善赋。我们所熟知的“燕京八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据说就是金章宗钦定的。这表明了金人汉化的程度。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并没有改变古汉语及其传承的语言,而是导致入声和浊声的大量消失。
元大都话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蒙古军在攻打金中都时,这座古老的具有代表性的幽燕古城邑,也就是老北京的前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历经蓟、燕都邑,秦广阳郡、东汉幽州、隋涿郡、唐范阳(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历史名城,被兵火毁于一旦。
1260年,夺得汗位的忽必烈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到燕京,以金中都东北郊水泊中的琼华岛上所建的离宫——大宁宫为驻所。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废弃金中都城,并以琼华岛大宁宫为中心,另筑新城。汉人刘秉忠按照《周易·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念建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次年,忽必烈将正在新筑的城定名“大都”。
老北京人自己受冤枉的时候,常有一句话叫作“我比窦娥还冤”,这句话,来源于元代的戏曲大家、大都人关汉卿笔下的杂剧《窦娥冤》。关汉卿大约生于金末,去世的年代约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之后。当时的元帝国将治下的百姓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色目人包括唐兀人、畏兀儿人、康里人、钦察人、斡罗思人、阿速人等;汉人包括北方的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南人,则指南宋遗民。关汉卿虽然属于第三等级,但从职业来说,就属于最低等级了。那时元帝国将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关汉卿就属于几乎是最底层的“老九”,仅在乞丐之上。
元代,自唐代实行的科举制长期被取消,儒生也就失去了入仕立业的机会。为了生活,当时的儒生也只能混迹江湖。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大都的儒生,就是其中的几位。他们为教司坊所属的戏班子乃至民间青楼歌妓写杂剧,写曲子,倒也成就了一代“元曲大家”。当年的积水潭(当今的后海、什刹海)岸边的歌楼酒肆、瓦舍勾栏,就是关汉卿等杂剧作家经常出入的场所,也是他与著名女艺人珠帘秀说戏、演唱曲歌的伤情地。
现如今,我们听不到大都话的语音,但却可以见到写于元大都的文字。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楔子》:“……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从这些文字来看,几乎丝毫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最早见诸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关汉卿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之句;张好古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之句。
元代的大都话,并不是蒙古语,而是在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幽燕语”基础上,受蒙古语、突厥语影响而形成的。
在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声韵》中,将元代北曲用韵分十九部,并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该书每部的字均按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排列,以入声分别派入阳平、上、去三声,记述并反映了元代北方话的语音实况。成书稍后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为元代燕山(北京)卓从之著。该书也是曲韵北派的代表作,亦分十九部;但它只将平声字分三类——大抵以阴、阳两调相配的字另立“阴阳”类,无相配的字归“阴”类或“阳”类,实际上平声只有阴、阳两调。
“内城话”和“外城话”
现代意义的北京话是在明、清逐渐形成并基本定型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由徐达和常遇春统领的明军攻占元大都,大都改为“北平府”。“北京”之名,起源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燕王朱棣登上皇位以后,将北平府改为“北京”,称“行在”。这里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北土城至长安街一线)的基础上营建的,移变成德胜门、安定门一线至前三门一线。
将首都从金陵迁到北京,始于永乐元年;那么,“北京话”之名,也当始于此。
伴随着迁都,大批江淮籍的官员、兵将进驻北京,使原来的大都话又增添了江淮话的成分。此后,来自山西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区。
北京的外罗城,建成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防蒙古俺答部侵扰,原本想建造环北京大城一圈的外罗城,因经费不足而只建了北京前三门以南的外罗城。由此,北京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
明代北京,大批外来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为官,带来了外乡省方言的语音。北京宛平知县沈榜在其著作《宛署杂记》卷17《方言》条目中记:“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这一记述,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北京城内居民五方杂处和各路方言混杂的状况。《宛署杂记》中收录的当时的北京方言词语,计为80余条,其中有些是来自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外地的方言,如“妗子”(舅母)等。在当时的北京方言中,“父亲”的称谓有三种,即:“爹”、“别”(平声)、“大”。语言学者认为,“爹”为原住居民语,“大”则来自山西,“别”来自江淮语。现今北京话中常用的“爸”,在当时并未出现。
不同地区的汉语方言,如江淮话(包括南京话、安徽话等)、山西话及冀东话等,在明代融入了“北京话”语系。
北京的“内城话”和“外城话”有别的现象,形成于清初。
清太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改女真族为“满洲”(简称“满族”),在沈阳(盛京)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此后,皇太极在“满洲八旗”之外,分别增设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汉八旗,主要成员为辽东人,其官兵所讲的语言,大多为源于幽燕语的辽东语(又称沈阳语)。辽东语源于冀东语,冀东语源于幽燕语。而辽东语又有别于冀东话,因为它是受女真语影响的变体。
清入主中原,以北京为都。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谕:“除八旗投充汉人外,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居住。”于是,北京内城(“前三门”以北)的皇城以外,变成亲王、郡王、贝勒与八旗官兵及眷属的专用地。被迁出内城的非旗人官民及原居民,居住在“前三门”以南的外城。由是,清初的北京话也就分成了两个区域性语言板块——“内城话”和“外城话”。
北京内城居住和驻防的是旗人。爱新觉罗·瀛生(笔名常瀛生)在《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中说:“清初满人入关,在北京形成了‘满语式汉语’。”康熙时代,满洲八旗在汉化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汉八旗官兵及“包衣”(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群体)等。他们说的,是汉八旗的沈阳话,而讲出来的则是满语和沈阳话相掺杂的语言,也就是“满语式汉语”。
到了雍正和乾隆时代,满洲旗人已经使用双语——既会满语又会汉语。与此同时,满语词大量进入汉语。如:“挺”“萨其玛”“逞能”“撺掇”“敢情”“嚼谷儿”等。
在满清入主中原十余年后出生,并在其后40余年内成为作词209首,有“清代第一词人”之称的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是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明珠之子,为康熙朝进士、一等侍卫。他在掌握汉文化和语言方面,应该算得一个传奇。纳兰性德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如《采桑子》:“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梁启超评纳兰词:“容若小词,直追后主。”王国维说纳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人物口语,有许多清雍正、乾隆时期北京话的特征。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话说黛玉“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戴。’”其中的“顽”,等同于现今的“玩”;“姨太太着我”,即现今的“姨太太叫(让)我”。个别语词有别,但意思可懂。再如《红楼梦》中用的“才刚”,已在如今被颠倒成“刚才”了。
基本摆脱“满洲式的汉语”,形成北京“旗人语”的时间,大约在道光、咸丰时期。代表当时北京方言语的文学作品,是满洲镶红旗人文康(别署燕北闲人)成书于道光中叶的《儿女英雄传》。如该书第八回“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中:“安公子此时的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样。假如姑娘说日头从西出来,他都信得及,岂有个不谨遵台命的?忙答应了一声,一抖积伶儿,把作揖也忘了……”其中几乎全都是当今的白话,只是将“寻根究底”写作了“寻根觅究”;将“抖机灵”写作了“抖积伶儿”,但近似或音同,只是多了一个“儿化”。
我们常说的“京韵京腔”,可在京剧的唱腔和念白中体验。徽班在乾隆年间进京以后,并没有形成纯粹的“京腔”;直到道光年间楚腔(又称汉调)进京与徽班合作,形成了“皮黄戏”。由此,皮黄戏被称为“京腔”。随着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在北京形成繁荣局面,剧中的“京白”使北京官话呈现出独特的京腔京韵,并使其成为后来的普通话的标准音。
清代,原本生活或搬迁到北京外城的住民,大多为明代遗民,说的是明代北京方言。相对从关外而来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明代遗民就成了“北京土著”,而“土著”讲的话,就是“北京土语”;若溯其源,北京土语为“幽燕语”的传承,幽燕语为“幽州语”的传承。
关于北京土语,可见戏剧家、北京文史风俗专家齐如山先生的专著《北京土话》。土语的语音,我们可以从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里领略一二:“哎,那(音“内”)天我你去啦,赶上你没在家。我溜溜儿等你半天,你压根儿也没回来。我一看褶子啦,我就撒丫子啦。”
轻声和儿化
轻声和儿化,是老北京话的显著特征。轻声,也叫“轻音”,即某些词里的音节或句子里的词,念成又轻又短的调子。北京话里,轻声字(弱读音节)在整个音韵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双音节词,两个音节的轻重程度大多不同,相比而言,前一个音节较重,后一个音节较轻。如北京话说的:老实、鼓捣、尾巴、窝囊、豆腐等。
北京话里轻音的作用有多种,其中有改变词义和词性的:如,名词的“言语”,即说的话,轻声后的“你言语一声啊”(你说句话啊),原本的“名词”变成了“动词”。轻声后动词变成名词的,如,“不要把精力花费在没用的地方”,其中的“花费”为动词;若变成“天天买零食也是不小的花费”,这“花费”就变成了名词。
所谓“儿化”,就是后缀“儿”字,但不自成音节,而是只表示一种卷舌作用,使韵母“儿化”。
齐如山先生在《略谈国剧无声不歌——兼谈念字法及小字辙》中说:“说某某胡同,则说本音,如泛泛说胡同,则说胡同儿。”如:我们说“家在茶食胡同”,不儿化;若说“我们家就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儿里”,加儿化。对此,齐先生有一系列举例:三条腿,儿化为“三条腿儿”;喝豆汁,儿化为“喝豆汁儿”;“票友”,儿化为“票友儿”等。
语言学者认为,北京话的儿化,是唐代的幽州语、辽金幽燕语的传承。明代晚期,儿化音已显成熟。北京的满洲旗人在初学汉语,特别是在说汉语“儿”时,会显出“大舌头”腔调,因为遇词尾的“儿”,他们不习惯“儿化”,而是将其单成音节。
昔时,老北京专营煤行的多为河北定兴人,澡堂里的服务人员的多为河北宝坻人。其词语带“儿”字的,不是“儿化”,而是单成音节。如煤行的定兴话:“一清早儿,摇了五百斤煤球儿。”当年北京胡同的孩子学说定兴煤行话,说煤铺伙计是“摇煤球儿的(音‘地’)”。澡堂的宝坻伙计招呼顾客:“修脚不?还有个蜡头儿(敷脚的热石蜡)呢。”这两地的方言,都属于辽金时代古老的幽燕语系。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追究一下辽燕京话或金中都话,是不是听一听定兴话和宝坻话的语音就能有所体验呢?
老北京话语汇中的儿化,很有讲究。比如“门”。北京的城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广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一律不儿化;但有三个城门例外,一个是“东便门儿”、一个是“西便门儿”,还有一个是“广渠门儿”。这种“儿化”与不“儿化”的区别,当是明清北京口语的习惯成自然。
而宅院的“门”,则一律儿化,如大门儿、二门儿、关门儿、开门儿、前门儿、后门儿。如果用反了,将永定门叫成“永定门儿”,或将“后门儿”说成“后门”,就不成“北京话”,甚至闹笑话。
再有就是“闪音”(也有叫作“吞音”的),即舌尖向齿龈轻闪而成。如说前门外的“大栅栏”,老北京的口语音为“大什蜡”;或者在快速的口语中,“吞”掉中间的“栅”(什)而为“大儿腊”,或“大腊”。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当今广安门立交桥附近的滨河公园,在金代宫殿遗址竖立着“北京建都纪念阙”。以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计,至建纪念阙的2003年,为850年。若以西周时代的蓟燕古城计,北京城建的日子就在3000年以上了。
从蓟燕语,到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到明、清北京话,及当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多少腔调音韵的溪流汇成了北京语言的长河。
普通话化,是当代新老北京人语言的总趋势。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近几十年来,北京内城、外城,远近区县及多个部委、大学、军队大院,除少数地域,大多已经普通话化。与此同时,由于求学、工作等因素,原本就属于移民城市的北京,又增添了多少新的“乡音”。外来语词,电脑语言、网络语言,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北京流行语。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