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口述 马宝林(余敦康妻子) 记录整理 艾兰(余敦康女儿余楠的笔名)

余敦康
学人小传
余敦康(1930—2019),湖北汉阳人。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52年随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在中学任教多年,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汉宋易学解读》《易学今昔》《周易现代解读》《魏晋玄学史》等。
从1978年老余被调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到2019年他因病辞世,差不多是四十年,而我们相遇相伴的岁月,也正好是这四十年。我想,这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安排。提起那四十年间的点滴,我都还历历在目,却又不知该从何谈起。想了想,最后决定还是谈谈我所了解的他这个人:他是个有责任感、有事业追求、有组织、有纪律、有担当的人,作为学者,无论生活中还是学术上,从来都很严谨。
他有思想,特别对玄学情有独钟。他说:“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所说的,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得到情感的满足。”他在生命轨迹中,也在寻求属于他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
儒道“会”通
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如何处理儒道之间的矛盾使之达于会通,成为玄学清谈的话题,也是老余对于玄学思辨的焦点。离他的生活最近的儒道“会”通,则是宗教所儒教室和道教室每周的聚会。

余敦康(左)与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合影。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们住在东单的一个大杂院里,距离中国社科院不远。每周二是所里固定上班的日子,一到这天,老余人在哪儿,哪里就热闹。从最初的几个人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儒教室与道教室不由自主地聚成儒道“会”通的聚会。大家清谈阔论,兴致勃勃。在社科院一直聊,还不尽兴,一行人就边聊边走,走到东单我们的蜗居,继续边吃边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有酒有菜,虽居陋室,无曲水流觞,但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在清谈之中碰撞出的火花,成了大家从事学术研究的思想源泉。伴随着“文化研究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道会通的观念,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老余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和《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两本书,这是他用心写的,不是用脑子,他在学术研究中投入了他的理智与情感。他在不断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柴米油盐与浪漫爱情
和老余结婚前,我是北京汽车工业公司的职工,一个性格张扬、独立生活的女青年,而这个博览群书的男人改变了我后半生的轨迹。
1978年,我们经朋友介绍相识。那年,他48岁,我38岁,这样的年龄,那样的时代,要建立一个家庭,对于我俩来说,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对他,对我,这个过程都既是理智的了解,又是情感的满足。
在我们交往的时候,他说:“生活是否有意义,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决心让他有意义他就有意义。如果说终究有命运,我们就是命运的主人。”那时候他给我的一封信里有一段他对婚姻的憧憬,让我至今看来都心潮澎湃:“让我们的家成为宇宙的中心,让我们的感情成为生活的轴心,但我们仍是有事业心的,这个事业就是做一个星际的航行者,历史的遨游者,世界的旅行者,我们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有鲜花,有音乐,有文学,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让我们两个人成为永远不知疲倦的对话者,让心灵的闸门永远敞开,让思想感情的交流永远畅通无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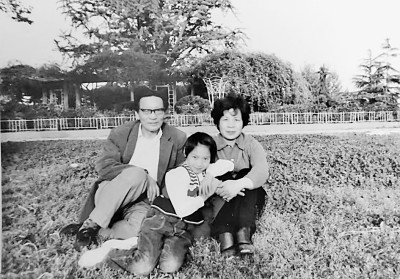
余敦康(左)与妻子马宝林(右)、女儿余楠在一起。
这段浪漫主义的畅想深深吸引了我,我们终于决定做命运的主人。1979年,我们结婚,很快就有了女儿余楠。从两个人变成三口之家,他对我的承诺,都兑现了,他是我这辈子值得依赖的人。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没有那么多浪漫。他对工资收入、工作职称一向看淡,“文革”后第一次提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的机会,他都不让我争,而那次分房正值我们两个单身需要走到一起之时。而不争的结果,是单位领导主动了解情况,最后根据我大龄、晚婚、少数民族、对方单位无房等条件,把房子分给我了。就这样,我们顺理成章走到一起。他说,如果你非要争一件事情,那即便争赢了也是输。
他说我是儒家,他是道家。我问,儒家和道家的区别是什么?他说,儒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道家是明知不可为而不为。这不过是他中年糊弄我的说辞,他在年少轻狂的时候,虽然不争名利,但因直言而遇到的坎坷何其多。
得意忘言
因为理智的坚持与情感的任性交织,老余这一辈子是比较坎坷的。他很喜欢苏轼,或许是欣赏这位屡遭贬谪仕途不顺的文人士大夫面对逆境的精神吧。
1930年,老余出生于湖北汉阳,父亲经商,小时候家境还可以,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在时代的洪流里,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如一叶扁舟。早年丧父,长兄到外地求学,老余与母亲、姐姐妹妹相依为命,虽有些困顿,但简单的生活也很有乐趣。他像当时的很多爱国青年一样,在求学的过程中慢慢萌生出文化救国的愿望。但是,老余的大哥从西南联大毕业回来后,想让他学理科,老余却想学文科。长兄如父,在哥哥的强压下,老余第一次反抗,独自离家,从武汉白区翻过一座山,跑到了红区参军。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段记忆,等我们的女儿长到青春期,老余见我批评女儿,就会“捣糨糊”,不让我说她。女儿走了,他就说我:“你说她干吗?离家出走了,你到哪儿找?你还活得成吗?”晚年的老余柔软了许多,他也说不清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是儒家的坚持还是道家的任性。
参军后,部队领导看他文笔好、有想法,把他从保卫科调到了宣传科。老余开始发表文章,展现出在文字与思想上的专长。然而,生性耿直、爱好自由的他并不适应部队生活,不久就离开了。
离开部队后,兜里没几个钱的老余打了几斤散白,搭了一个拉棉花的驳船。在那一船棉花顶上,他喝着酒,仰望着空中恣意变幻的游云,随着亘古东流的江水漂泊。人世流水、浮云苍狗,他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用什么方式救国?——用文化!”从那时候起,没读完高中的他决定要考大学,要考哲学系。哲学,是他敲开世界的门。
1951年,老余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后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了他一开始就向往的北京大学学习哲学。大学期间,他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可毕业的时候没能留校,被分到了天津一所中学教书。他想要继续读书做研究,下决心报考北大的研究生,因为本科成绩优异,最终被北大破格直接录取。
老余1956年重返北大。在北大校园里,青年学子们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他给武汉大学的朋友写了四封信。后来,这四封信被一位朋友找到了,信中写道:“现在,我觉得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领域,过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有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人的独创性得到承认、鼓励和法律的保护,这种生活在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是第一次有了,所以这是一种从理智到感情都能确实感到的真正的幸福。”可见,那时的老余是多么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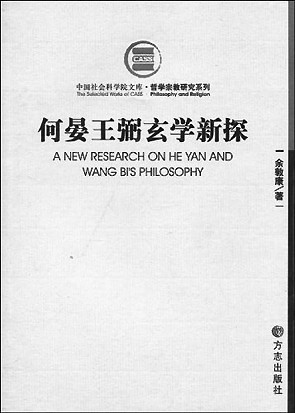
不久,老余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母亲也跟着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计划好将母亲从老家接来北京,还准备送母亲一把梳子、一副老花镜。结果,这三个简单的愿望都没有实现。自幼和母亲关系极为亲厚的老余,没能实现对母亲的诺言,这让他始终难以释怀。在那段时间,老余囿于生活的困境,无法静心思考玄学,但对于魏晋玄学家们的命运,对于阮籍、嵇康诗文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情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心态,有着一种切身的感受和强烈的共鸣。
好在经历这次打击的老余,并没有一蹶不振。一段时间之后,老余又回到了北大。那时候,他跟着任继愈先生编辑整理《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虽然没有太多精力搞自己的研究,但也正是整理那些资料的过程让他积累了大量知识,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只可惜,没多久老余就又被分配到湖北汉阳平林中学教了八年的书。
1970年,老余拿着介绍信辗转多地,风尘仆仆地赶到平林,生活环境一夕剧变,却并没有怨天尤人,在平林中学,他交上了不少朋友。当时一起工作的韩道生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们常聚在一块喝酒谈天,老余在教学上解答了他的许多疑问,他们还一起参加学校的劳动,一起过节,一起旅游。那时候,不光周围的同事,就连学校的学生和附近的乡亲也都喜欢老余,爱听他讲话,直到几十年过去,他们还都记得老余是个“活字典”。
一直到1978年,48岁的老余才正式被调回北京,到宗教所工作,真正投入他所热爱的学术研究。他说自己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因此对这来之不易的研究机会无比珍惜。我甚至觉得,他对研究专注到了近乎极致的程度。
但依旧因为他的性格,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87年举家迁去南京。在南京大学,他同样遇到问题,1989年重回北京,宗教所还是敞开了怀抱。这是深厚的缘分吧。这时我也来到了宗教所工作。这次归来之后,便是文章前面提到的宗教所儒道“会”通的欢乐与积极思辨的学术氛围。
历经半个世纪的坎坷,到晚年,老余在玄学研究上无形中摸索到“得意忘言”的境界。“意”是指把整个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是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去探索天人新义。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与此同时,教育观点也渐渐成熟。
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
老余有很多段教书的经历,早年教过小学和中学,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科院带硕士生、博士生,晚年在北大给本科生讲授哲学导论,还给一些企业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他不喜欢那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更喜欢潜移默化的引导,这也是他不自觉地承接北大的传统。
他为学生讲哲学导论,谈到“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这没有确定的答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哲学结合,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也造就了哲学的不同。所以他引用金岳霖先生的话,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老余不愿意用自己的成见去“误导”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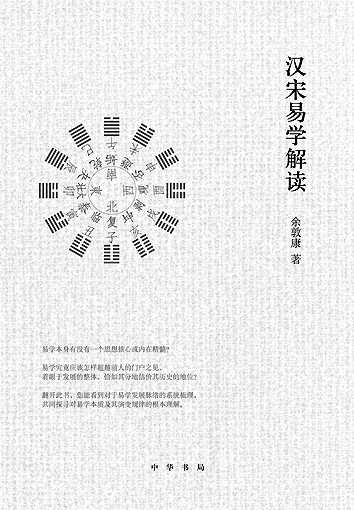
他希望他的学生拥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开放的心态,特别是要有一种对中国文化慧命的执着,对传统与创新的不懈追求。这是属于北大的学风。时隔半个世纪,他回忆在北大求学的往事,“一切都变得依稀仿佛,如雾如烟,但是唯有这颗在北大所承接的文化的种子以及对玄学的钟爱始终未能忘怀,因而也一直把北大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
随着传统文化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老余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慢慢多了起来,他有时也去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讲学。他参加过会议之后,总有人会津津乐道地谈起会议的“花絮”,老余如何扭转乾坤、一锤定音;如何在讨论中提出问题,挑起争论;老余拍桌子了——会议上两派争论得不可开交且不成体统的时候,老余突然拍案宣布:“散会!”让陷入牛角尖而不自知的学者们骤然停止争论,且慢慢回过味来,大有禅宗棒喝的效果。
他珍惜能将中国的文化精神推广出去的机会,但这样那样的事务没有占去他的太多精力,不论什么时候,他的注意力还是在哲学上、在他研究的学问上。
他有一篇后来被多种文集收录的文章——《回到轴心时期》,在文中,他展望着:“人类文化必将形成一种高度和谐的多样性的统一,是一种‘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文化,一方面千姿百态,具有各个民族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思路,不同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共同的价值取向,表现了共同的人性本质,是人类可以优游于其中的共同的精神家园。”
他穷其一生,不断追求理智的了解与情感的满足,知行合一地探求着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及阴阳二气所构成的和谐统一。

老余很欣赏张载,他反复跟我提的是张载在《正蒙·太和篇》里的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以及最知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讲世界观,“为生民立命”讲人生观,“为往圣继绝学”讲继承内圣心性之学,“为万世开太平”讲由内圣心性开出经世外王。而老余这一生,走到最后是“和”,与不同思想的“和”,与自己人生的“和”,儒心道骨的“和”,“名教”与“自然”的“和”。
老余晚年曾跟我讲,“我写了八本书,带了一些学生,我没有白来一趟”。他去世的那天,我早上醒来,看到他正在望着天花板微笑。
我想他是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的,他的人与天在一起。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