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肖复兴(《人民文学》杂志原副主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作为写作者,故乡在情感的记忆里被酿造和孵化,最终在文字中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写作者的还乡。还乡,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之一。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德莱塞和索尔贝娄的芝加哥,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还有我国老舍的北京……那里都是他们的故乡。没有他们的故乡,就没有他们的文学作品。
但是,对于写作者,故乡不必也不能如水漫延,过于庞大。我更注重的故乡应该是福克纳说的那样一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如奥兹的特里宜兰,陈忠实的白鹿原,师陀《果园城记》里的小城,甚至更小如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斯坦贝克的罐头厂街,只是一条小街巷。
这样的想法,是22年前的冬天,我重返老街之后逐步形成的。这条老街叫西打磨厂,位于北京前门楼子东侧,紧靠着以前的护城河和明长城。这是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明朝建都北京修皇城而聚集来自房山打制石磨石器的石匠而得名。我从小在那里长大,一直到21岁半去北大荒。从北大荒返城,又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一共住了24年。那时候,老街拆迁在即,院门前贴满拆迁的公告,院墙上刷有白灰书写“拆”的醒目大字。
那一刻,想起1930年林志钧为陈宗蕃《燕都丛考》一书所写的序言,开端说了这样一段话,他曾经住过的宣武门外“老墙根地旷多坎陷,其接连上下斜街处,则低峻悬绝,考辽金故城者,辄置为辽南京金中都北城墙址”。接着,他历数上下斜街曾经的名人居处,具体写了一段下斜街的土地庙:“庙每月逢三之日,则百货罗列,游人摩肩接踵,与七八两日之西城护国寺、九十两日之东城隆福寺,同为都人趁集之地。”这些地方,早就不复存在。即便当初老城墙尚在,但还有多少人知道是辽金古城金中都的城墙旧址呢?所以,林先生发出如此“莼衷怅触”的感慨。我更是怕拆迁之后,老街变脸,如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诗中所叹:“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
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暗想,幸亏老街还在,大多老街坊还在,如果再晚来一步,就什么也看不见。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条明朝老街呢?

乔家票号全国总号“大德通”旧址。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摄
老街只有1145米长,却是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的商业街,以饭店和旅店多而著名。北京八大楼之一福兴楼,有名的冷饭庄福寿堂,都在这里。当年北京旅店共有101家,前门一带有75家,这条老街上就占30家。远的不说,民国时期,学者邓云乡来北京住的兴顺店,就在老街的西口。1949年5月,诗人邵燕祥从河北正定到北京工作,住老街路北的招待所,是以前的“利顺德”二层木楼的老旅店。
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叫不上名来的年画店、刀枪铺、胡琴作坊、铜铺、铁厂、厨房、诊所、药店、醋房、绱鞋铺、制帽铺、小人书铺、糖果厂、豆腐坊、油盐店、粮店、文具店、染料房、剃头铺、鼻烟店,还有京城最早的民信局和银号,以及玉皇庙、关帝庙、铁柱宫,专门祭祀鄱阳湖神萧公堂的几座老庙,粤东、临汾、宁浦、江西、应山、潮郡六大会馆等,都鳞次栉比地挤在这条老街上。如果我不去写写它们,还有多少人知道、关心它们?
尽管风云跌宕中,这些地方大多变成大杂院、小学校或改作他途。但是,这些旧址不少尚在,有老街坊还在这里住着,我正好可以和他们聊聊,把即将被打散的记忆收集回来。那时候萌生一个小小的野心,希望像路德维希写《尼罗河传》一样,也能为老街作传。
一晃,22年过去了,陆陆续续写了几本书,包括《蓝调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捌章》(2007年)、《我们的老院》(2016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18年)、《燕都百记》(2021年)等。但是,老街传尚未写成,一直萦回在梦中。
这么多年来,我不止一次重回老街。有时候约上在老街上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回老街走走,看看,聊聊。孩子从国外回来探亲,我也愿意带他们回老街,他们的根是在这里的。尽管老街西半部已经完成了拆迁后的整修改造,老院落所剩无几,但东半部基本是老样子,一些老街坊和他们的后代至今尚在。每一次走到这里,就像重返童年时光,见到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格外亲切。特别是老院拆迁翻盖一新,大门紧闭,进不去了,老街坊让我踩在她家的床上,从后窗翻进,又从后窗翻回她家的床上,她都不让我擦一擦踩脏的褥子,而是拉着我说话,说着老院老街的往事,说起我小时候爬上房,在她家房顶上疯跑时她骂我们的情景……这些总让我感动得想落泪,忍不住一次次重回老街,一次次打搅他们。
尽管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县,尽管我的青春岁月是在北大荒度过的,但前者是我父辈生活的地方,是我填写履历表的籍贯,后者我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我始终把这条老街当作我的故乡,那里是我的情感所重所系的地方。

冯氏家宅。解放初期,瑞蚨祥的东家孟老先生曾居住在此。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摄
反复回老街,陀螺一样,只在老街转,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这里。比如,我一直认为老街上除了西口的前门第一宾馆是座老洋楼,其他的都是平房四合院。实际上老街一共有六座多层的洋楼,均为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影响下盖起来的。建筑是历史遗留下看得见的印记,风雨百年之后,与老街传统四合院并存,在北京城众多老街上难得一见。
加拿大学者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了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失去活力。”她特别强调:“必须保留一些各个年代混合的旧建筑。保留这些旧建筑的意义绝不是要表现过去的岁月在这些建筑上的衰败和失败的痕迹……这些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她还说,这些旧建筑“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真的是难得,老街保留下这六座洋楼,让一段历史没有被湮没,让流逝而去的看不见的时光以有形的建筑存在,让我对老街有了带有历史感的新认知。
老街上,乡村饭店和和平饭店也是奇特的存在。它们名字叫饭店,其实是两个大院。这样的名字,只能是当年和平解放以后起的,和以前老院相比,看名字就能看出年代的包浆。这两个院子,都是拆除了老街原来一片低矮破旧的老房后盖起来的。里面住的人家,也和以前那些大院里不一样。乡村饭店住的都是部队干部和家属,和平饭店住的是银行和评剧院的工作人员。
从外观看,乡村饭店比和平饭店更气派,院墙是水泥拉花,大门两旁,东西两侧各有四扇和两扇西式高窗,外装铁艺栏杆,两扇对开的红色大门。关键在于大门上方,嵌有一个大大的红五角星,有棱有角,饱满立体,和老街上其他的老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是以前再威风的老宅院断然没有的。乡村饭店,以这样一个大红五角星的标志,引领老街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样的住房格局,带动老街住户的变化。住进的这些新人,从穿着打扮、说话口音、走路姿态就能分辨出来,和街上原来的住户形成两种不同群体。
有意思的正在于这一点。我忽然发现,老街上,院落不同,不仅暗含着住在里面人员身份的不同,更注定着日后命运的不同。乡村饭店、同泰店和我住过的粤东会馆,可以成为三个代表。乡村饭店里住的部队干部包括老红军及其家属子弟。粤东会馆里住的有工程师、技术员、翻译家、中学老师、小学校长、职员、会计、火车司机……同泰店里住的基本是在火车站扛大个儿的,即搬运工,还有蹬排子车的,或者拉大车、赶马车运货卖苦力的工人。
这是三座建造于不同时代的院落:粤东会馆建于清代,同泰店建于民国,乡村饭店建于新中国成立之时。时代的分野,地理的肌理,一一被时光雕刻,镌印下百年沧桑的一册断代史。这册断代史,既属于老街,也属于北京,乃至是国家的一个注脚,有人有事,有情感,有细节,有反思,有话可说,有案可稽,雪泥鸿爪,活色生香,百味俱生。
想到这一点,我发现多年来一次次重返老街是值得的。只有在这样一次次的重返过程中,才像烙饼一样,不停地翻个儿,将饼烙熟,让自己的笔有个结实的落处。我将这样的过程当作还乡。我不大赞成所谓的精神还乡,精神总要有个实在的落处,就像鸟落在枝头,不能总在天上云彩间浪漫地、大写意地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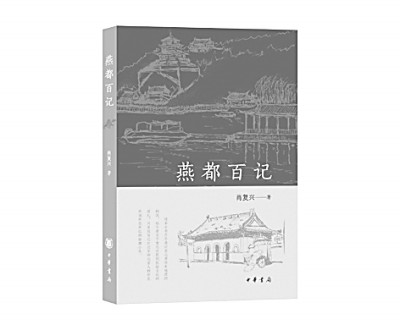
散文集《燕都百记》
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有故土,有故人,有故事,有归属感的地方。为什么要一次次还乡?因为那里有割舍不掉的回忆、感情和生命。在这样一次次实实在在的还乡中,而不仅仅在典籍的纸面上钩沉,也不是走马观花的采风所能奏效,你才有新的察觉和发现,才对你自认为熟悉的故乡有新的体认,让你的回忆融进更多人的回忆,让你的感情更丰厚而富有质感,下笔就可能不虚。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论及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个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看到意义,这一能力就是诗人的职业特征。”在偌大的北京城,老街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有百年沧桑的历史,更在于一次次返乡时,让我逐渐有了一些能力,不断地看到它、感知它与体认它。那些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融入了记忆和感情。因为那里有我的记忆,也有老街那么多老街坊的记忆。那里有我的感情,也有老街那么多老街坊的感情。那里有我的故事,也有老街那么多老街坊的故事。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6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