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面面观·新媒介与文艺经典化】
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学理路径
——在大众评论、原生理论与总体文学史三维空间里推进
作者:江秀廷(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特聘副教授)
网络文学的批评标准与评价体系问题、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是近十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议论纷纷,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后者,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视角、方法,得出差异极大的结论,不过围绕经典化问题的学术探讨也提升了网络文学的研究深度。既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点:在文学批评层面,评价主体及其持论依据多具有精英化取向,即专业学者依然在传统文学的坐标系里审视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理论层面,从理论到批评的倾向明显,这些理论既可能是传统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创造性借用,也包括超文本诗学、粉丝文化和媒介环境学说的跨语境阐释;在文学史层面,很多学者用“发展史”代替“文学史”,并用资料汇编和作品批评选本的方式临时“占位”,普遍认为网络文学史的写作“时机未到”。
在我看来,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和经典化应当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自下而上”地开展研究工作,暂时悬置“诱人”的理论,从文学作品、大众评论和文学事件等文学活动实践出发;二是采用系统性的、综合性的原则,即在大众评论、原生理论和总体文学史的三维空间里推进“网络文学经典化”这一学术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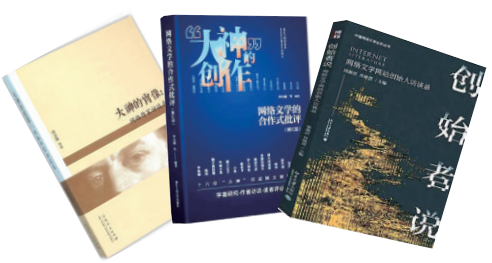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大众评论: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地基作用
数字媒介显然是推动网络文学大众化写作的重要动因,其消除了写作者专业、学历、性别、职业等方面的身份限定,也赋予读者大众参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权力。那么,什么是大众呢?学界对大众的认定往往局限于普通读者,进而将他们围绕网络文学作品的评说归结为大众评论(或网络批评、网生批评)。其实,除了普通读者,网络作家、网站编辑等“专业”群体也应该被纳入进来:前者基于创造经验的、指向叙事的文学理念往往更具体、更有效,如愤怒的香蕉(曾登科)、跳舞(陈彬)、流浪的蛤蟆(王超)等网络作家在知乎平台上的“解答式”评论常常一针见血地回答读者疑问;后者则能更好地把握行业发展动态和法律制度,在网站评论板块设置、商业机制、产业化途径等方面更具发言权,阅文集团、龙的天空论坛、17k小说网等都在此方面作出重要探索。从大众的评论形式上看,不论是“即兴式短评”“体悟式点评”,还是“鉴赏式长评”都应值得重视。这些评论文字可能存在于商业文学网站中由段评、本章说、书友圈构成的“章说系统”里,也可能在豆瓣读书、百度贴吧、新浪微博、微信公号等相对独立的网络阵地。大众评论实践实际上发挥了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地基作用,学界在推选作品、设立标准、遴选典型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这座富矿。
与印刷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单向性不同,网络文学的大众评论是多向的、交互的,无论是黎杨全强调的活态文学观念、社区性及“2.5次元的文学”,还是李强提出的“链接性”,都能在大众评论的交互性上呈现出来。网络文学经典化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这与评论文字的无限衍生、交互有着密切关联。更进一步讲,大众评论动态交互特点还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始终伴随着创作,用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生产性批评。其生产性体现在大众既能在评论过程中不断为作家提供素材和写作思路,还能创作同人文本,将批评与创作融为一体,这就引发我们思考:网络文学经典化,除了作家笔下的主文本,是否还应该包含伴随文本、副文本?二是大众评论往往包含着消费行为,大众评论推动网络文学经典化除了依靠文字传达观念,还能够以多样的消费行为标记自己对作品的支持度,点赞、角色红包、打赏等就是最直观的表现。三是大众评论往往与大众的触觉有着密切关联,手指与屏幕的接触,是内在的触觉意识和外在的触觉符码的统一,超越以视觉为主导的传统批评而指向一种可称之为“触觉批评”的新批评范式。
网络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逐层筛选的过程,大众评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最基本的支撑作用。无论是文学网站的排行榜,官方组织的“影响力榜单”,乃至于多方合作举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都是以大众的评论意见及相关数据为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大众群体在各类社交媒体的推文传播,有助于推动建设中国长期以来并不完善的书评系统。书评系统的价值不仅能够让更多国内外读者迅速了解网络作家的写作特点和作品的叙事内容,还是后期视听转化、游戏改编等产业化的重要参考。
原生理论:从大众评论实践中进行理论凝练
大众评论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和具体现象的阐发层面,网络文学经典化还需要从感性言说提升到理性的理论建构层面,这就涉及创作规律的总结、理论话语的生成乃至于美学范畴的凝练等多个方面。基于大众评论的、网络空间生成的原生理论,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理论范式。崔宰溶在《网络文学研究的原生理论》中指出,所谓原生理论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原住民自己的理论,它所强调的是对其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力,将大众的思维提升到“理论”高度。原生理论常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话语生产,一是对网络小说叙事语法的规律总结和网络文学产业发展方向的预估。批评话语往往以“话语簇集”的形式呈现,如围绕着“爽文学观”,大众群体在网络空间里提炼出“金手指”“玛丽苏”“代入感”“升级”等话语,这些文论“关键词”已被逐步应用到学术生产体系中。同时,原生理论往往建立在幻想类、历史类、现实类等网络类型叙事之上,指向大纲和细纲设定、爽感表达、人设技巧等方面的规律,如齐橙从工业题材的“硬核”叙事出发推及所有题材:小说题材的区分,其实就是原生理论内在逻辑体系的区分。
大众总结出的批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直观的、经验的且不成系统、比较零散,因而需要专业批评家、理论家的“入场”提炼,使之成为公认的学术话语。目前,学界逐渐认识到原生理论的重要性,或以“粉丝学者”的姿态从大众评论实践中进行理论凝练,或进行合作式的“理论生产”。最为常见的合作方式是专家学者对网络作家、编辑及网站负责人进行访谈,诞生了《大神的肖像:网络作家访谈录》(周志雄)、《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邵燕君)、《网络文学的合作式批评(浙江篇)》(单小曦)、《对话:走向网络文学经典之路》(李玮)等成果。透过对话,网络文学相关从业者的观念主张、批评理论得以展示和总结,原生理论得以完善、丰富。正是对原生理论的重视,学界摆脱了长久以来文学理论的“场外征用”及由此导致的“强制阐释”,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范式因而得以成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合作式研究”的策略正在得到“推广”,如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组织开展的“阅评计划”,就不再是传统的、以专业批评家为核心的作品研讨会,而是给予平台负责人、编辑、专家、粉丝读者充分的发言机会,这显然能够更为全面地呈现文学创作、接受、传播的真实情况。
经过大众评论的筛选、原生理论的合作式生产,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彻底解答,但也为我们指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学理路径,并在一些局部得到验证。如网络悬疑推理小说作为网络小说中的重要类型,其评价标准及其经典化问题在大众评论和原生理论的观照下已有初步的答案,具体来说包含智性、社会性和批判理性三个层面:一是故事好看,即悬疑设定、解谜策略、人物塑造等方面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推理逻辑有着超凡之处;二是能够反映广阔的社会内容,尤其是将社会现实问题纳入文学叙事中,以一种同情、悲悯的文学品格打动读者;三是超越低层次的欲望写作模式,上升到理性批判层面,引发人们深层的思索,乃至于推动社会的法治建设、文化心理等社会议题的解决。
总体文学史:超越传统的、静态的文学史编写模式
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相比,文学史作为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和价值载体,其对文学经典的塑造、定位往往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权威作用。网络文学经典化同样离不开文学史为其“背书”,但现有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又很难将网络作家、作品纳入其中。精英化的文学史观念,如将作品的原创性、陌生化和思想性视作能否入史的标准,就会遮蔽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艺术价值,造成今天网络文学经典怀疑论和网络文学不能写史、入史的偏见。这种主观决定论的、静态的、片面的文学史观需要改进,即由专业批评家、学院派文学史家主导的传统文学史写作,转向吸纳包括大众评论、原生理论在内的总体文学史构建,这一范式重构应当在网络文学史料和文学史编纂方式上得到重点呈现。
网络文学的史料丰富多样,除了上文提及的大众评论,更包括网络文学论争、对话、大事件等。在网络空间里,很多网文爱好者基于自己真实的阅读体验、从业经验,撰写网络文学阅读史、网络小说类型发展史、文学网站变迁史乃至网络文学简史。尽管这些“史”并不追求资料的全面、理论的深刻和体例的规范,论述过程中也不讲究客观公正,但能够在颇具个人化的评论中揭示着局部的真相。在网文编辑、网站负责人乃至网文作者参与下,网络文学史写作呈现出开放、多元的面向,并与专家的文学史写作构成互补关系,为最终“成熟的”网络文学史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weid(段伟)费时一个多月在龙的天空论坛撰写的长文《一部标签的丰富史,一则原创小说类型谈》堪称代表,该文不但回顾了网络玄幻、武侠、穿越、重生、现实等类型小说兴起的背景、代表作品,还从一个阅读者、网站运营者的角度明确回答了“网络小说是什么”“为何网络小说的核心是类型小说”“类型小说重现的背景”“类型小说的商业优势”等问题。同时,网络空间中的论争和事件也应受到足够重视,如围绕“玄幻事件”“文以载道”“九州香蕉论”“55断更节”等论争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材料。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文学史料的挖掘,推动我们采用网络民族志(网络中的田野调查方法)的研究策略深入写作、评论现场,在书评区、读书论坛获取一手资料。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其诠释学著作《真理与方法》中首先提出“效果历史”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在印刷媒介时代,接受美学所期待的效果史、接受史、批评史、文学史写作面临着真实的困难: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评价活动难以及时呈现,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的完型往往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和少数专业批评家的笔端。数字媒介给予大众发声的机会,也使得总体文学史写作成为可能,因而总体文学史的编纂方式应该超越那种传统的、静态的文学史编写模式,更多地体现出链接性特征。如同网络文学的社区性、交互性,总体文学史应当同样以动态性、开放性、数字性的形态呈现。唯其如此,网络文学经典化才能以符合其本身特质的方式最终完成。更为重要的是,由大众评论、原生理论、总体文学史构成的学理路径,不仅能够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命题提供“解题思路”,也能为网络文艺、新大众文艺的评价标准、经典建构、学科建设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4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