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李庆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员)
编者按
海洋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海上贸易将全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重要的港口城市,承担了物流中转、商业服务等功能,亚洲地区也不例外。尤其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一些港口城市得益于显著的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参与海洋贸易,获得大量财富,甚至发展成为半独立乃至独立的政权,有学者将这类靠海洋贸易立国的政治实体称为“港口国”或“港口政权”。多年以后,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资源禀赋匮乏、开发能力不足、国际政治局势影响等因素,一些港口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这些港口的兴衰更迭,同样映射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本期文章选取东南亚地区的河仙、马六甲,梳理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兴衰历程,以期对近代港口的历史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17世纪60年代中国经历了明清鼎革,一些不愿意接受清朝统治的民众逃往海外。1671年,雷州人莫玖离开北部湾畔的家乡,渡海来到柬埔寨,而后在濒临泰国湾的河仙建立起独立性政权“港口国”,左右中南半岛的政治局势,在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鄚玖、鄚天赐经略“港口国”:政治、经济与文化
世居雷州半岛的莫氏是北部湾畔的名门望族,明清易代之际,南明政权与清军在北部湾沿海进行30余年的争战。1671年,莫玖17岁,“不堪胡虏侵扰之乱”,来到商人船舶聚集、贸易兴盛的南荣(今柬埔寨金边),获得真腊国王的重用,不久莫玖请求到下柬埔寨恾坎(即河仙)发展,被委任为“屋牙”(地方长官)。莫玖从今天柬埔寨磅逊湾至越南金瓯角沿海地区招徕流民,建立富国、陇棋等七村社,初步确立河仙政权的地盘。1679年前后,暹罗东侵,莫玖屡经离乱,一度被掳至暹罗。1700年前后,重回河仙,四方商民慕名归附。1708年,莫玖向广南阮氏称臣,阮主许为属国,名其镇为河仙,以莫玖为河仙镇总兵玖玉侯,莫玖改名鄚玖,以与越南名声不佳的莫朝相区别。
鄚玖统治时期河仙不断壮大,建筑堡垒,凿掘城壕,装备军队,确保境内安宁,成为中南半岛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他曾到西班牙人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学习西人施政及自强自卫之法。在经济上注意招集流民,采取轻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把境内土地分配给本地民众,提供农耕用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湄公河下游冲积平原大片荒地得到开发。18世纪中叶曾经游历越南的法国人波微说:河仙地区已成为勤勉之人民安居乐业之处,森林被开垦,荒土变成良田,从河川所引之运河四通于田间,而丰裕之收成予农民以充足之粮食,且为殷盛商业之货物。
1735年,鄚玖去世,终年81岁,他的儿子鄚天赐继承父业,执掌河仙政权,袭封总兵大都督、钦差都督琮德侯。河仙名义上属高棉,又向广南阮氏称臣,但是鄚氏自置官署,自辟幕府,自建军队,自主经济,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越史纲鉴考略》介绍“港口”“为我大南附庸,传子天赐”。鄚天赐曾自称“高棉王”。
17、18世纪西方人称河仙为Can Cao,清朝称之为港口国。《清朝文献通考》称“港口国”“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鄚天赐爱好文学,开“招英阁”,“招徕四方文学之士”,最著名的有十八位,时称“十八英”。法国学者保尔·布德说:“在鄚玖的努力下河仙不但变成一片可居地,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鄚天赐又进一步把它改造成一个文化中心。”
河仙的海上交通与国际贸易
17、18世纪,中南半岛湄公河三角洲-暹罗湾兴起西贡-嘉定、美湫、河仙、大城等新兴港口。河仙发挥濒临泰国湾、连接湄公河的河海联通优势,海上交通与贸易网络覆盖了湄公河三角洲-巴萨河流域、柬埔寨内陆地区、马来半岛东部沿海地带、廖内-林加群岛以及巨港-邦加地区,远及印度洋东海岸、东北亚的日本。
河仙鼓励自由通商,实施低关税,“招徕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商人被分为三类,赋予不同的经营业务:大商人经营长途贸易,中小商人经营本地贸易,官商则专营国家垄断商品和对外贸易。在鄚天赐时代,河仙被誉为“海陬之一都会”,“胡同穿贯,店舍络绎,华民、唐人、高棉、阇(见图一)类聚以居,洋舶江船往来如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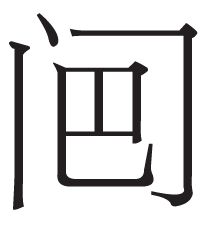
河仙与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均有贸易往来。1728、1729年,鄚玖曾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获得对日本贸易的“信牌”(朱印状)。而河仙与中国的贸易多集中于广东、福建两地。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每年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的帆船有30艘左右,其中85%~90%是广州驶往河仙港口与交趾支那,交易物品包括稻米、锡、藤条、西米、各种涂料等。1758—1774年,广州从东南亚进口锡79935担,其中从河仙港口进口24688担,数量仅次于巨港(47468担)。18世纪70年代,巨量的锡源源不断地从河仙港口运往广州,推动了广州锡器制造业的繁荣。
越南将暹罗湾及其以南地区称为“下洲”。河仙、暹罗与缅甸之间的传统交通路线,陆路从六坤(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府一带)、车加陆前往缅甸,海路则经阇婆、红毛(英国人)诸国海岛,穿越马来半岛东海岸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着马来半岛西海岸抵达缅甸。阮朝嘉隆八年推出《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可见“下洲”贸易商品种类甚多,有官府控制交易的金、银、象牙、犀角、豆蔻、砂仁、苏木、乌木、红木等贵重物品,也有丝茧、绢布、砂糖、沫糖、石块糖等紧俏商品。
“港口国”消亡:东南亚“非经典政权”之归宿
18世纪60年代河仙境内战事不断。越南西山阮氏政权崛起,广南阮氏屡吃败仗,颠沛流离。1771年,暹罗郑昭发兵攻陷河仙,鄚天赐被掳,后自杀。其后河仙动荡,昔日繁华荡然无存,鄚氏后人子泩、公柄、子添等先后被广南授予河仙镇守,但地位今非昔比。1808年,阮朝派官领河仙镇事,改变了“鄚氏世袭”的惯例,河仙纳入越南版图,“港口国”退出历史舞台。
东南亚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各种类型的政权和国家,长期受国际学界关注。有学者提出马来世界海岛地区存在爪哇式和苏门答腊式政治模式,以及“河流流域脉络体制”等理论,有学者发现室利佛逝和马六甲海峡地区政治中心、王国的首都常常在几个重要贸易港口之间转移,马来历史的政治是不稳定的,政权存在时间很少能超过百年。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提出15至17世纪东南亚港口城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或者成为某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发展成为半独立乃至独立的政权,这些靠海洋贸易立国的政治实体,可称为“港口国”。与此类似的是,美国学者万志英将马六甲等海峡政权归类为“港口政权”。
很显然,这些在政治制度与政权结构上“残缺不全”的政治实体,不同于传统大陆帝制国家的“经典政权”,可视为“非经典政权”。河仙“港口国”就是一个例子。17、18世纪鄚氏父子乘中南半岛动乱之机,立足河仙,建立起具有独立地位的“有海港的繁荣公国”,但两传就走向消亡,归根结底是因为河仙地区疆域狭小,缺乏立国的基础,特别是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本地缺乏丰厚的资源禀赋和足够的生产能力,过于依赖海洋贸易与海外市场,易受外围因素的冲击。而缺乏天然屏障的劣势,也使得港口国在柬埔寨、广南阮氏、暹罗等国家的夹缝中求生存。此外,河仙地区多种族、多宗教的社会结构,也很难建构起像“经典政权”那样大一统的政治文明、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缺乏坚实稳固基础的政治体经不起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冲击,东南亚多数“非经典政权”都有类似的命运,鄚氏港口国也不例外。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4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