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从“经验科学”到“精确科学”
——於崇文院士的地质人生
作者:杨润聪 刘宁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於崇文(1924—2022),浙江宁波人。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长期从事理论地球化学、区域地球化学、地球化学动力学和地质系统复杂性研究,将基础地质和矿床学研究提升至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理论层次。著有《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动力学》《地质系统的复杂性》等。

2013年,於崇文在做学术报告。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13年,耄耋之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球化学动力学家於崇文走上讲台,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师生讲授成矿系统复杂性研究的最新进展,精神矍铄,数小时不倦。这不仅是一次学术交流,更是一位老科学家与后学晚辈的薪火传递。
在那次报告上,他勉励众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也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写照。於崇文毕生追求的,就是将地球科学中看似“简单”的问题重新提炼,将其凝结成具有科学深度的秩序与复杂性,推动地球科学从“经验科学”走向“精确科学”。
考入西南联大
战火中的地质启蒙
於崇文祖籍浙江宁波,1924年2月15日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名字凝结着父亲於淮山的殷殷期待——“崇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国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淖之中,家境虽不宽裕,但於父於母深知教育的重要,尽其所能将七个子女悉数送入学堂。
於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但也很开明:“只要不越轨,就不加干涉。”课余时间,於崇文喜欢种花养鱼、饲养虫鸟,还动手制作蜡模玩具。在自由探索的宽松氛围中,他释放了天性,培养出对生活的热忱。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轰炸上海,於崇文一度随家人回镇海老家避难。才8岁的他,跟父亲到水塘边捕虾,去田里收割芝麻。由于父母长年在外奔波工作,於崇文自小便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学会了独立与担当。他的性格也在家风熏陶与时代风浪中逐渐成形:严谨细致,担当笃实,开放包容。这是他后来在地质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既能埋头耕耘又能广育桃李的重要缘由。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於崇文无法安稳求学,不得不跟随学校频繁辗转各地。无论境遇多么困顿,他从未动摇过对知识的渴望。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1940年至1943年,在日占区读高中的於崇文,深感屈辱。但他并未被压垮,反而更加奋发学习,努力寻求出路。
1943年6月,於崇文中学毕业,计划赴重庆投考大学。此行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加之身患痢疾,抵达浙江龙泉时,他已体力不支,只能在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暂作休整。龙泉突发鼠疫,於崇文错过了考期,只能投靠在湖南“中国零陵耐火砖厂”工作的二哥於崇业,等待第二年的大学入学考试。
正是在这段看似偏离人生轨迹的时光中,於崇文遇到了一位重要的引路人——北大地质系早期毕业生、湖南地质调查所专家靳凤桐。其时,靳凤桐正应零陵耐火砖厂之邀,勘查耐火黏土资源。於崇文每天跟着靳凤桐于山林间穿梭,爬矿洞、做检测。这次经历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通向地质科学的大门,心中关于地质学的种子悄然萌发。
1944年6月,日军逼近零陵,并且大学考期将近,工作未满一年的於崇文前往重庆。经过两天三夜的颠簸,他终于到达重庆参加考试,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这年秋天,於崇文抵达昆明,开启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入校伊始,於崇文听了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国事前途”的主题报告,热血沸腾。他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然而,当时西南联大条件十分艰苦,入学不到一个学期,於崇文便因感染伤寒,不得不休学一年。
复学后,早年在湖南随靳凤桐体验地质考察的奇妙之旅催生出对专业的追求,於崇文毅然改学地质地理气象专业。西南联大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由原北京大学地质系和清华大学地质系重组而成,师资力量雄厚,有德国岩石和构造地质学家彼得·米士及袁复礼、王烈等名师任教。在与这些名师的频繁接触中,於崇文锚定了一生的学术航向。
在北大
坚定学术志向
1946年秋,北京大学复员回迁,於崇文进入地质系继续深造。父亲过世,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但他始终牢记8岁那年父亲的教诲:“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於崇文重新燃起了斗志,逐渐走出父亲过世的阴影。带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与父亲的遗愿,他像在西南联大时那样,不管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在地质学里不断探索。
当时的北京大学地质系汇聚了一批国内顶尖的地质学家,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系统学习了地质学的基础理论。黄汲清先生的构造地质学课,以生动的语言与富有感染力的手势将复杂原理拆解为可感的时空叙事,深深吸引着於崇文,他总是提前坐在教室前排,全神贯注记录笔记。孙云铸、王鸿祯两位先生的古生物学课程,用化石演化解读远古生命,让远古生命栩栩如生,极大增强了於崇文对生命演化的兴趣,他常常独自来到地质陈列室,端详每一块化石。斯行健先生构建了鲜活的远古植物世界,其对古植物的熟稔与授课激情,深深感染着於崇文,让他明白“任何一个细微的发现都可能蕴含着重大的意义”。在地质系外,申又枨、王湘浩、庄圻泰等先生的数学课程,极大提升了他的定量分析能力,磨砺了迎难而上的学术韧性。郑华炽、霍秉权、马大猷等先生的物理类课程,则培养了他实证研究的思维习惯和对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理解……这些学养深厚、风格各异的顶尖学者,通过严谨的治学态度、生动的教学方法以及对基础理论的重视,系统塑造了於崇文的地质学素养。更为关键的是,他深刻领悟到学科交叉的潜力和价值,培养了宏观洞察力与微观严谨性,为日后在地球化学与动力学领域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根基。

2005年,於崇文(左2)带学生下矿井进行地质考察,左1为刘宁强。 图片由作者提供
於崇文并未将自己局限于书斋。课堂之外,他追随恩师与同窗,走进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次次攀山越岭参与地质考察,将脚印深深镌刻在广袤的大地之上。在野外实践中,他真正理解了岩层的肌理、地貌的语言,也明白了地质学不仅是纸上的图表,更是脚下的泥土与心中的山河。在那些严苛的训练中,他学会了如何用罗盘判断山体的方向,用锤子敲开岩石的秘密,用笔和图纸记录大地的年轮,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带入现实,又在现实中不断打磨知识的锋芒。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织,使他的学术之路逐渐清晰,也让他的理想之火在野外的晨曦与暮色中愈燃愈烈。
北大的经历,不只是求知的时光,更是精神成长的滋养。在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中,於崇文始终践行着他“在北大多学一点”的誓言,山野间探索的足迹与实验室里钻研的长夜,是他对誓言的坚守。在北大,他不仅习得了解析复杂地质现象的能力,也铸就了一生受用不尽的治学态度与创新精神。他开始关注地质学的前沿问题,尝试用自己的理解去叩问自然的深层逻辑。
1950年,於崇文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是去一线单位从事野外地质勘查工作,还是留在北京大学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思及自己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忆起师长们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他决定服从学校安排,留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是他学术人生的新起点。
留校任教后,於崇文迅速投入教学与科研工作。他深知,教学不能仅停留于传授,科研也不能游离于教育,唯有二者相辅相成,方能真正培育出有思想、有能力的地质人才。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常亲自带领学生奔赴野外考察,让他们在山川之间、岩层剖面之中直观感受地质学的魅力,并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学生心中点燃探索自然奥秘的火焰。
孤寂的路
潜心基础理论研究
伴随新中国地质教育体系的重建,1952年,於崇文调任至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肩负起结晶学、矿物学两门课程的教学重任,他“自导、自编、自印、自演”了一套教学方法:自己确定授课内容,自己编写教材讲义,自己刻钢板油印讲义,最终再以生动讲解呈现于课堂。他所奉献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教育理念。
1955年,北京地质学院决定开设全新的地球化学课程。彼时中国的地球化学领域尚属一片空白,无课程、无教材、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於崇文凭借扎实的矿物学和物理化学基础,义无反顾接过“开荒”的旗帜。他边学边教,一边向苏联专家学,一边吸收其他国家学者经验,在教学内容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兼容并包。最终,於崇文高质量完成了教学任务,编写出国内首套地球化学教材,为后续教学提供了宝贵蓝本,也为中国地球化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石。
面对国际地球化学理论与方法的快速发展,他找到了自己长期的学术方向:在基础理论中探求真理,在学科交汇中拓展边界。那时,众多同行投身“找矿”热潮,於崇文选择了另一条孤寂的道路——基础研究,他深知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根基,只有筑牢根基,才能使地质学这座大厦屹立不倒。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已经成为一名老师的於崇文,拿出上学时的那股钻研劲头,下定决心,从头学起,没日没夜地汲取各类跟地球科学相关的知识。
20世纪60年代末,和北京地质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工一样,於崇文奔赴江西峡江县仁和镇干校劳动。从讲台到稻田,从地质图纸到锄头农具,於崇文一如既往认真投入,从不敷衍。1971年,於崇文被抽调至福建教改小分队。他深入闽南地区主要矿山,收集第一手地质资料。这段贴近实际的经历让他再次反思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以及如何解决复杂地质问题的客观需求。他将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结合理论整理、编写成贴近实际的矿床学教材,与地质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向他们传授矿产资源知识,也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段时光,于他而言不仅是一场学术上的“再出发”,也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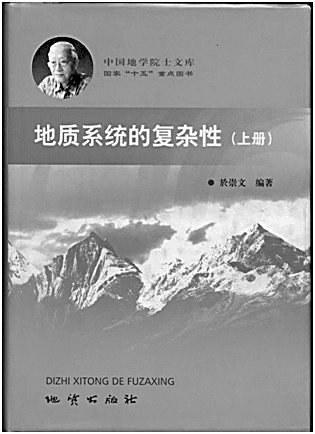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偶然获得的讯息激起了於崇文内心深处的学术涟漪:中国科学院的气象学者正在尝试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气候变化,这与他长期思考地质学向定量化、精确化发展的努力方向不谋而合。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将多元统计分析运用到地质学中,或许能够助推地质科学向定量化方向迈进,为这门古老学科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於崇文迅速组建团队并选定陕西略(阳)—勉(县)—阳(平关)地区的煎茶岭镍矿床作为研究对象,从野外地质、室内鉴定分析、数据处理到实现地质学和数学相结合的地质数学研究,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为了搜集国内外的最新文献资料,他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各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当时,图书馆尚无复印设备,他便将厚厚几本专著逐字誊录,字里行间是对知识最深沉的敬畏。对野外采集的标本样品也是一样,从标本碎样、光谱拍摄、显影、读谱,直到定量数据提取——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操作,确保原始数据准确无误。为进行数据的计算机处理,他奔走于北京各单位和河北正定之间,从编制地质数学的计算机程序到实现运算,一气呵成。他还在保定为冶金部开办化探电算训练班,培养出一批能够运用数学地质方法处理化探数据的技术骨干。然而,於崇文的目光并未停留在应用层面,他又进一步整合研究成果,将其拓展至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编写系统专著。於崇文用了整整四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总计145万字的鸿篇巨制《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地质与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这本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地质数学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为我国地质科学迈入定量化时代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攀登高峰
摆脱模糊与经验的桎梏
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具备高度的可重复性与精确预测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地质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被视作描述性的科学——主要依靠野外观察、标本采集与岩性描述。於崇文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曾听一位学者感慨:“地质学是一门不科学的科学。”这句话让於崇文明晰了毕生的学术使命:要让地质学摆脱模糊与经验的桎梏,成为一门可以精确衡量、可重复严密验证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为此,他开启了一场历时数十载、将基础理论与前沿方法不断引入地质学的征程。
如前所述,於崇文注意到应用数学中多元分析研究的蓬勃兴起,以及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率先在我国系统引进数学地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使得国内的地球化学研究沿着更加科学化、精准化的道路前进。多元统计分析在地球化学界迅速得到广泛应用,为地球化学研究提供了全球视角和便捷工具。
在新科学理论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於崇文注意到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协同学理论,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前沿理论对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他在非平衡、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基础上,吸收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区域地球化学理论与方法。从1982年到1985年,於崇文参与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南岭地区有色、稀有金属矿床的成矿条件、成矿机理、分布规律及成矿预测研究”。作为该项目二级课题“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的负责人,他于1987年出版专著《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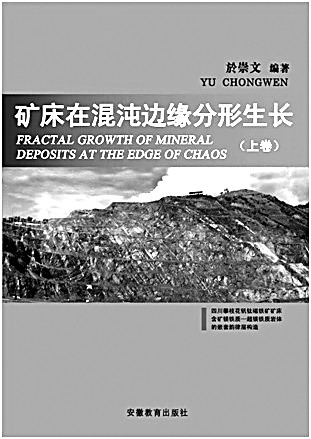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渐渐出现了新的转变趋势——从平衡热力学转向非平衡热力学,由热力学转向动力学。80年代初,於崇文将动力学与成矿作用相结合,提出“广义地球化学动力学”的新定义,并在我国率先将其引入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将矿床成因机制从静止和定性的情态分析提升到动力学研究水平,开辟了“成矿作用非线性动力学”的矿床成因研究新方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先后出版《云南个旧锡-多金属成矿区内生成矿作用的动力学体系》《热液成矿作用动力学》《成矿作用动力学》三本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他还在国内首次设计并完成相关模拟软件系统,开拓了矿床成因理论和成矿规律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成矿作用动力学”领域的学术基础。
在当时的学术界,复杂性研究非常薄弱,从事复杂性研究的研究人员更是屈指可数。面对长期以来“地质学不够科学”的偏见,於崇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要使地质科学由“经验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唯有将基础自然科学、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理论与地质科学相结合,才能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飞跃。他长期探索地质现象的本质和地质科学的基本问题,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出“地质作用及其时空结构是一切地质现象的本质与核心”,进而将复杂性科学中的四大前沿理论——自组织临界性、瞬态混沌、混沌边缘、弱混沌引入地质研究,构建起具有原创意义的“地质系统复杂性理论”,最终出版了《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一书,在方法论层面推动了地质学从经验归纳走向定量建模的科学跃迁。
於崇文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矿产资源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成矿系统复杂性理论——“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这个理论揭示了矿产资源形成与演化的复杂规律,为可持续资源开发提供了前沿理论支撑。自2006年至2015年间,他先后出版《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南岭地区区域成矿分带性》《南岭地区目标斑图式区域成矿分带》等专著。
於崇文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大致归纳为四个阶段:经验事实的总结,现象的归纳和演绎,普适性理论与方法的建立,抽象为数学形式体系和哲学思维的飞跃。回顾自己的地质学研究历程,於崇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当时自己的研究只停留在第二个层次,那是一个注重经验的层次;30年后,自己处在第三个层次并要矢志不渝地朝着第四层次努力。他说:“只有当地质科学能够建立起数学化的理论体系,‘地质科学是不科学的科学’这种说法才会真正烟消云散。”於崇文用半个世纪的探索,给出了那个萦绕地质学界百年命题的终极答案——“地质科学是科学的,是一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科学”。这是一位科学家的学术宣言。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8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