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
学人小传
田世英(1913—1994),安徽砀山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1936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1940年毕业。历任江苏徐州中学教师、四川教育科学馆二室主任、四川大学副教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编审局地理组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编辑室主任,山西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所长。主持编写新中国第一、二套中小学地理教材,著有《中学地理新教法》《四川文化教育地图》《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地理学新论及其研究途径》《小学地理教学法》《世界长河》《中国历史地理讲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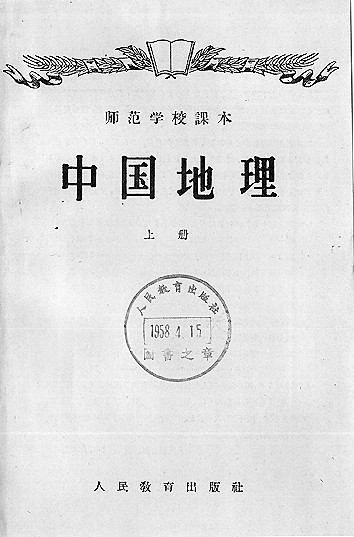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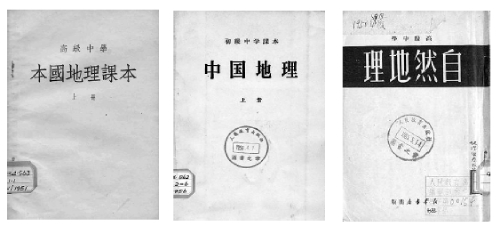
田世英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第一、二套中小学地理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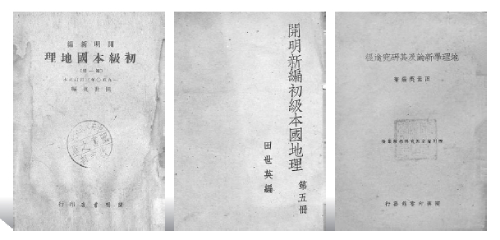
田世英编写的开明版地理教材以及编著的《地理学新论及其研究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地理是中小学必修课,不仅初中、高中要学,小学高年级也要学。当时各校使用的是国家统编教材,主要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田世英是这套地理教材的主要负责人。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事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不少值得回味的瞬间。
生于砀山 求学名校
田世英1913年出生于江苏砀山(今属安徽)。其父是清末秀才,很重视子女教育。田世英早年上私塾,后入砀山第一高小、县立初中。他回忆,1925—1927年读初中的时候,在上海读大学的大哥每逢寒假回家,总会带回一些进步书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新星月刊》《新女性》等,打开了他的视野,“对思想和学习,都是大有帮助的”。(田世英《敬怀锡琛先生》)
田世英高中就读于著名的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今徐州一中),学校设普通、师范两科,他上的是六年制的师范科。这是一所名校,校长严立扬治校有方,延揽了一批名师,如国文老师胡哲敷、历史老师姚步康、地理老师厉鼎勋、数学老师蔡介福、物理老师钱秀之和严晓帆、化学老师张蔚之、英文老师封介人、美术老师孙瘦石和陈竹珊、体育老师许凤飞等。(见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编印《徐中》)其中,胡哲敷对田世英影响最大,尤其在扩展课外阅读和提高写作能力方面。一次,胡老师布置了一道作业题,要求精读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刊出的《文章病院第一、二、三号病患者》,写出心得,并对照自己本学期的作文,逐篇加以检查,为自己的文章诊断一番,看看有哪些毛病。同学们一开始看了这道题都觉得好笑,文章的毛病也能进医院治疗?但当田世英在父亲指导下读完此文后,不禁大为赞叹:分析得清楚,诊断得好!从此以后,他家里每年都要订阅《中学生》,每期他都是从头看到底。此外,他还买了《开明文学辞典》《开明国文讲义》《文心》《国文百八课》《中学生文艺》等课外读物。
通过大量阅读,田世英逐渐学到了写文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写作兴趣和习惯,中学时代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短文。他后来从事编辑工作,不断为青少年编写地理通俗读物和地理课本,都与青少年时期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并不断创作有很大关系。(田世英《饮水思源忆开明》)
随迁陕西 且学且教
1936年,田世英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地理教育生涯。七七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先后迁至陕西西安和汉中,并入西北联合大学,田世英也因此到了陕西。大学期间,他不但勤奋学习、参与实践,广泛涉猎有关知识,而且刻苦钻研、不断创作,撰写了《怎样生聚与教训》《江苏砀山产梨概况与今后改进刍议》《野外考察日记》《集训得来的三点新认识》《庆祝师大三十七周年的两点小认识》《陕西城固姜黄产区之研究》等文章。其中,他在《怎样生聚与教训》(1936年)中讲“抗日图存”,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如果自己没有实力,只一味赤手空拳地讲公理、道正义、求人援助,实在是一种自求灭亡的政策!所以现在我们要想救国,想要图存,非下一番生聚教训的苦功,去培植国家的实力,发扬民族精神不可!”“生聚是物质的建设,教训是精神的培养。”“生聚”主要指“复兴农村”与“准备战争的武器”;“教训”是指“教训知耻复仇的意识和国家的意识”与“教训战争的常识和技能”。在《江苏砀山产梨概况与今后改进刍议》(1937年)中,田世英对家乡特产“砀山梨”的产业概况、梨区分布与产量、品种与栽培方法、易遭的几种灾害、运销方式等做了概述,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创立梨作试验场、扩大栽培面积、设立联合运销机关和罐头工厂等。
那时,田世英不仅在西北联合大学读书,还在中学担任地理教员。他紧紧抓住学科教学目标这个核心问题,引导学生朝着深处、广处思考。他说:“几年来在中学教地理,每逢和一班新同学上第一课的时候,我总先问学生:‘地理是什么?’‘地理有什么功用?’”学生常见的回答比较简单和肤浅:“地理是记载山脉河流物产的,我们读地理可知道哪里有山,哪里有河。”或者说:“地理书上可以告诉我们某处有通某处的道路。”对此,田世英会启发学生:假若我们读地理的目的仅在于知道某处有山、某处有河,那么知道新西兰岛上有一座山,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功用?不知道又会如何?如果说“地理书上可以告诉我们某处有通某处的道路”,那么地理的记载还不如路标或旅行指南写得清楚明白,对于海上航行的情形,地理学家甚至不如水手知道得清楚。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到:地理和历史是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重要科目,而且,地理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功用:供给人类向自然界求生的经验,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利器。
田世英不仅依照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教授学科知识和技能,而且时常带领学生到野外考察乡土地理。在他看来,地理教师“率学生到野外考察地理,为教授该科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如果教师不善于领导‘考察’,往往变为‘旅行’和‘玩耍’,不唯考察的目的达不到,并且失掉地理真义,而学生精神散漫,心猿意马……的确,考察地理是一件难事,率领一班毫无经验的中小学生,更是一件难事”。作为地理教师,田世英认真总结了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考察的经验和做法,比如考察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出发前要向学生交代所需工具等事项;应如何对学生提出要求,如不准逾越考察区域,严守考察时间,并告知成绩评定的方法;野外考察时,教师的态度要严而可亲,诲人不倦,居于辅导地位,要多用比较法;考察归来,要开检讨会,让每个学生作报告总结,并进行考试和评定,有必要的话可办一个展览会……(田世英《教材及教法:中学地理科野外考察的研究》)
田世英在中学的教学、教研经历,为其以后编写地理教科书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下巴蜀 结识叶老
1941年,田世英应聘至四川教育科学馆从事编研工作。时任馆长郭有守(子杰)聘请来不少在巴蜀避难的名家,如叶圣陶、朱自清等作为专门委员,编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科教育丛刊、丛书和课外读物,其中《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就是他们在这里工作时创作的。如此氛围,刚出道的田世英自然是不甘落后,勤奋有加,他结合专业及教学经历,撰写和发表了《中学地理课本的选择标准》《地理的功用》《中学生宜读的地理课外读物》《中学地理科野外考察的研究》等文章,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文史教学》《中学生》等杂志上。同时,他还撰写出版了《中学地理新教法》《大战图说》《四川文化教育地图》等书。由于表现突出,田世英被任命为四川教育科学馆第二研究室主任。
田世英在四川工作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叶圣陶,并在叶圣陶的指引下走上了编研地理教材的道路。《叶圣陶日记》1941年8月18日记载:“阅同事田世英君之书稿一册,略为修润,并指出其应改正处。田君于地理教学颇有经验者也。”在三年共事过程中,叶圣陶不时指导他如何搞研究、写文章,还常常谈起开明书店。有一件事田世英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一天,馆长拿着顾颉刚先生的一篇大作,十分得意地交给叶老,并说顾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文章得来不易,要放在《文史教学》的显著地位发表。叶老笑嘻嘻地接过稿件放在桌上细细地阅读。我注意他看了顾文以后,并无“先睹为快”之感,皱了一下眉头,放在来稿的卷宗里了。过了一阵时间,让我校对初排的校样,我发现并无顾先生的那篇大作,而我的一篇经叶老看过,让我重新再写的小作——《论地理课本标准》,却排上去了。这使我大为愕然,心里很纳闷,为什么厅长约来的顾先生的大作没有发表出来?我悄悄地问了叶老一声。他说,我们办刊物,做编辑工作,这样的事是经常遇到的,一定要把握好取舍的标准。咱们这个刊物是《文史教学》,不是《文史研究》。它的读者主要是文史地教师,不是专门研究文史地的专家学者。什么文章可取,什么文章不能取,既要为读者考虑,又要为作者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最怕的是以作者的地位、名望为标准。(田世英《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编辑——忆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
田世英首次编教科书,也与叶圣陶有关。1943年,教育部门向各出版社征集新版本教科书。为此,已离开四川教育科学馆、专事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叶圣陶约请田世英编写初中本国地理。叶圣陶把地理课程标准交给他,再三叮嘱要灵活处理,不能完全照搬照套,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应当拿出自己的主见,“他又把当时各书店出版的地理课本,在内容、结构、文字、可接受性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一向我介绍了一番。我立时感到,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编辑国语课本的内行和专家,而且对各科内容都了若指掌,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编辑——忆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对于此书的编写情况,《叶圣陶日记》在1943年上半年有多处记载。这套初中地理课本约45万字,分五册出版。叶圣陶对书稿做了大量修改,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特别是对地理课程标准里所列的一些条目,以及国民党政府大加宣传的内容,他支持田世英的意见,认为“教科书的取材都应当是真实的、科学的。我们不能进行指鹿为马地教育欺骗孩子,这是犯罪的!”“他又一次强调了地理课程标准所列的教材内容要慎重考虑,决定取舍”。(《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编辑——忆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送审之后,当局要求修改,叶老坚决不同意,就让他们另请高明编写。而田世英编写的教材改名为《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于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结果,解放区、国统区都有不少学校采用了这套课本。并且,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中,此书被正式推荐为中等学校地理课本,修订后一直使用到1952年才为新编课本所取代。
1943年秋,由叶圣陶推荐,田世英转任四川大学地理系副教授,1948年又转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其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地理学新论及其研究途径》(1947年),该书共分八章:地理思潮的演进及趋势、新地理的特性及其启示、新地理学的旨趣、地理因子分论、研究地理的基本条件与工具、专题研究撮要、实地考察、基本读物介绍及应备图籍。有评论言:“用作教科书,亦甚为相宜。”
转赴京华 教材新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之邀,田世英从四川来京担任编审局地理组组长,编修新的通用地理教科书,从此成为一位专业的教材编研者。来北京第一年,他加倍努力,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修订原华北解放区《高小地理课本》,形成《新编高级小学地理课本》(4册);二是带领赵寿祺、马宗尧新编了《高级中学自然地理》;三是与曾次亮合编了《初级中学本国地理》(4册);四是与武汉大学地理系邓启东教授合编了《高级中学本国地理》(上下册)。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田世英任地理编辑室主任,负责全国中小学和工农地理教材的统编和出版工作。当时工作人员还有颜廼卿、周光歧、黄竞白、褚亚平(借调)、马宗尧和侯峙(绘图)。他们用了两年多时间,不仅修订了前面的教科书,还新编了《初级中学课本自然地理》《高级中学课本外国经济地理》《人民民主国家地理》等,从而完成了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地理教科书的光荣任务。按照田世英的说法,这些教科书有三个类型:一是解放区所编印的旧课本的改造,如高小地理;二是新编写的课本,如初中本国地理与外国地理;三是改编外国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课本。(田世英《谈谈中小学地理教科书》)
新中国第二套地理教科书是全新的完整统编教材,数量和质量都较此前上了一个大台阶。195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调集全国力量编教材的指示,一批教育干部和学科专家被选调到人教社工作。从1953年底到1954年,地理编辑室先后新调入陈尔寿、叶立群、芮乔松、许冀闽、李明、沈崇歧、蒋允吉,并且借调了一些高校地理教育专家,从而完成了1956年颁布的中小学地理教学大纲,以及全套中小学地理统编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作为编辑室主任,田世英除了审阅、修改所有地理教材之外,还直接参与了其中四部教材的编写工作,即《初级中学中国地理》(上下册)、《高级小学课本地理教学参考书》(4册)、《师范学校课本中国地理》(上下册)、《师范学校课本自然地理》。配合教材使用,他又撰写了一些文章,如《谈谈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我参加了男三中的地理教学观摩会以后》《我们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收获和体会》《介绍“地理教具的制造与应用”》《我们在“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性质和目的”的学习中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精简教材进一言》等,发表在《地理知识》《人民教育》和《编辑工作》等杂志上,表明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理教育和地理教材编纂思想。
田世英认为,中小学地理教科书要具备“三性”:一是政治思想性。“地理课本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并不等于使地理课本变成政治课本。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选择教材、批判教材、组织教材的最高指导原则,并贯彻到全部教材里,成为教科书的血肉和脊髓;不应当成段地、生硬地,像镶花边一样地插在教科书里做装饰;不应当仅在绪论里,或编辑大意里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在正文内部却把这些话都忘记了。”例如,初中中国地理“东南沿海区”的“位置和地形”一节,在谈到祖国统一的必要性时,既从台湾国防地位重要性的角度讲必须统一,又指出了台湾是我们祖国神圣领土的不可分割部分,实现统一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二是科学性。“地理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科学,地理课本一定要有高度的科学性”,要达到这一要求,首先“要确实”,其次“反对夸大”,再次“反对空洞笼统”。三是适切性。要贯彻教学的可接受原则,“教材的组织和叙述,应当把握原则,突出重点”;“要适当附有图表插画和照片”;“名词要统一”;“度量衡单位要一致”。他还指出,“编好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的两个环节:一是学习苏联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的先进经验,一是走群众路线”。(《谈谈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对于苏联经验的借鉴,他提出“这两本书改编的重要原则,是使它中国化”;对于后者,他提出“各地优良教师所编写的教案,是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含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理论根据。我们的课本虽然不可能采取教案的形式编写,但是从教案中可以看出课本在教学实践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因此,我建议编辑同志们除了有计划地有目的地参观教学,了解实践教学情况外,还要大量征集各省市优良教师的教案,作为我们修订和编写课本的参考资料。”(田世英《我参加了男三中的地理教学观摩会以后》)
此外,田世英以“胡芸”的笔名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地球上的五带》(1954年)、《祖国的大地》(1955年)、《祖国的海洋》(195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6年)四本科普读物。1953年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主持召开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田世英当选为筹委会首席总干事。从1953年11月到1957年1月,田世英当选为北京地理学会第三、四、五届常务理事(理事长先后为孙敬之、王钧衡)。
执教三晋 遗篇传世
1957年,在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完成之际,田世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他被下放到山西运城稷山县农村,几年之后,到山西大学地理系教中国历史地理、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等课。在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田世英最大的安慰,是叶圣陶与他的友谊和交往。叶圣陶依旧与他保持联系,问寒问暖,信件来往不断。过去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和人教社工作时的老领导金灿然也很关心他。这时金灿然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组织和出版了许多经典古籍,他曾邀请田世英参与部分编辑工作。“文革”中,田世英的学术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山西大学史稿(1902—1984)》里有一点记录:“在动乱的岁月,一些老教师,如陈盛甫、姚奠中、郝树候、田世英等人,顶着风险,潜心读书和治学,为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取得学术成果准备了条件。”
改革开放后,人教社恢复了田世英的编辑室主任、教授职称和原工资待遇。20多年过去,此时的田世英已经66岁,本想离晋返京,山西教育部门极力挽留他,山西大学党委书记张念先、校长陈舜礼亲自到家里做工作劝说,田世英便决定继续留校任教,并出任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和首届所长(1982年),还担任了研究生和外国来华进修生的导师。田世英积极乐观,尽力延长学术生命,不顾冠心病多次发作,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出版《世界长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参与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一书的撰写,还发表了《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黄河流域古湖钩沉》《“东海为桑田”今释》《洪水与地名》《探讨山西黄土高原发展农业生产的出路》《河津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等论文。1988年初,田世英被山西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同年12月退休。1994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在山西太原逝世,终年81岁,留下了未出版的三部手稿——《中国历史地理讲义》《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国古代地理残稿杂俎》。
本文图片由田世英女儿田仪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2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