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学术争鸣】
作者:吴根友(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近期,《光明日报》连续刊发了孙向晨、傅永军、庞学铨三位学者关于汉语哲学讨论的文章,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章后,笔者比较同意庞学铨《“汉语哲学”三问》中的基本观点,即从广义的汉语哲学角度出发,多层次地解读汉语哲学的内容。在庞学铨文章的基础上,笔者想把有关“汉语哲学”的立场表达得更为鲜明、更带感情色彩,以彰显“汉语哲学”与大众常识紧密相连的一面。在笔者看来,“汉语哲学”就是用汉语言表达的哲学思想。这是“汉语哲学”的基本涵义,也是合乎大众常识的涵义。对于这一常识意义上的“汉语哲学”,我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加以阐发,凸显哲学的日常语言与专业语言的联系和区别,更好推进“汉语哲学”在当代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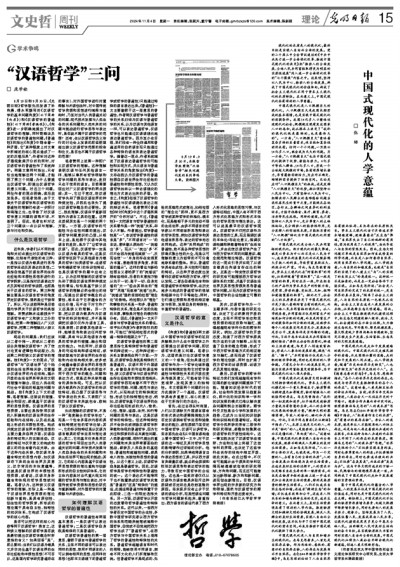
8月19日、9月30日、11月4日,光明日报哲学版围绕“汉语哲学”相关问题刊发的系列争鸣文章。资料图片
汉语哲学的历史维度
“汉语哲学”首先涉及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汉语本身是有自己历史的古老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因此,“汉语哲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区分为古代汉语哲学和现代汉语哲学。在黑格尔之前,西方学者几乎没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至多只是说中国哲学关注的侧重点与西方哲学不同,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认为,中国哲学更关注伦理学问题。因此,汉语能表达哲学,汉语有自己的哲学,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问方式虽然不是很恰当,但其背后的实质不是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而是质疑20世纪初一系列哲学史书写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所谓“中国哲学”,是不是“中国哲学”的固有形态?这种质疑的背后包含着多方面的问题意识,其中之一是主张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应是“以中释中”,即用合乎中国哲学自身要求的方法来诠释中国哲学。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分类中没有“哲学”这个门类,但无论是“六艺”,还是后来的“五经”,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知识。如果中国的知识系统中从来就没有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内容,胡适、冯友兰以及其他的哲学史家也不可能凭空虚构出《中国哲学史》。形象一点说,自古希腊以来,欧洲人用陶罐或银缸装着“哲学知识”,而中国则将“哲学知识”装在鼎、陶罐和后来的各种精美的瓷器里。
孙向晨一文给出了关于“汉语哲学”意义的规定,即汉语哲学要表达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依此规定来看,古代汉语哲学恰恰表达了古代汉语世界人们的生存经验。而古代汉语哲学所表达的生存经验,与古希腊语所表达的生存经验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讨论共同的问题,仅以“共同善”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为例,亚里士多德以城邦政治为基础,阐发了以城邦的共同目的作为城邦内所有人共享的“共同善”理论;而中国的墨家,则有感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而且“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的混乱现实,提出了以“上同于天”“下同于民”的“同义”为基础的“共同善”理论。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哲学实践,特别是由几代人构成的“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共同体,立足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传统——儒家传统而创建,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如张世英的“横向超越”说与“万有相通论”、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形而上学”、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的大伦理学与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世界制度论”的政治哲学……它们都是相当精致的汉语哲学,只是现代的欧美哲学工作者绝大部分都不通汉语,无法了解现代汉语哲学的成果,更无法与汉语世界展开深度对话。
毋庸置疑,现代汉语哲学还处在发展之中,当中国由古典时代的“中国之中国”、中世纪“亚洲之中国”,发展成为现当代“世界之中国”后,汉语哲学还将继续立足于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同时也将从中华文明的“文明”视角回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与人类共同问题,发展出新的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
论及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中国哲学,再提一个汉语哲学是否多余?又有人从英语世界的语言习惯出发,认为汉语哲学在英语当中都可以用Chinese Philosophy来表达,故而没有必要再重提“汉语哲学”,这是出于英语世界学人的理解的方便而提出的否定汉语哲学的理由。但庞学铨认为,这恰恰表明了汉语哲学的必要性,即哲学与语言的依存关系,也显示了汉语本身的细腻之处。笔者大体上认可庞学铨的观点,但觉得在此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虽然在英语世界之中,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可以用Chinese philosophy加以表达,但在汉语世界里,这个词的意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提出汉语哲学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有着学术意义与日常使用方便的意义。
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交集,这是因为“国家”总是与语言有关,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定义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几个核心要素当中,语言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当我们说“中国哲学”的时候,汉语哲学就自然而然包含其中。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空间意义与多民族文化的含义,是“汉语哲学”这一仅仅以语言为载具的短语无法涵盖的。古代“中国哲学”,从东汉以后包含着印度传来的佛教哲学,而“古代汉语哲学”就可以不包括印度传来的佛教哲学,只有汉语佛教哲学才可以包括在汉语哲学的短语之中。而现当代的“中国哲学(Philosophy in China)”就可以不包括大量翻译成汉语的西方哲学的内容。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两个术语所表达的内容又有重合之处。万物各自有体而分立,世界却是一体且交叉,人类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内容的交叉、重叠,合乎世界一体与人类生存本体之共性。另外,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两个短语所表达的内容,各有胜场,不必相互取代。在名实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有“循名责实”和“取实予名”两条路径。从“取实予名”的路径来看,“中国哲学”之名偏重于以国家的政治实体为基础来道说哲学这门知识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形式,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是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因此,当我们从政治实体的角度讨论“中国哲学”时,就理所当然地要涉及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最近郭齐勇主编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中,就专门列出“少数民族哲学”一卷,从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哲学”作了尝试性的新理解。可以说,在政治上属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哲学,都属于“中国哲学”。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16世纪后半叶及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用汉语写出来的介绍西方哲学的汉语言形式的哲学作品,就很难说是“中国哲学”,但如果说这些作品是“汉语哲学”,大体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像利玛窦用汉语写出的《交友论》《天主实义》两部哲学作品,将其视为“汉语哲学”中最早从西方哲学的视角融会中国哲学的汉语哲学著作,并不违背哲学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常识。在当代,当我们说“中国哲学”时,在日常语言层面,显然不包括大量译成汉语的一切外国哲学。而当我们说“汉语哲学”时,大量汉译的外国哲学是否属于汉语哲学,就是一个可以从哲学的专业角度加以讨论的问题。举例言之,今天中国哲学界大量翻译康德的哲学著作,有朝一日德语、英语世界的学者发现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那么汉语康德哲学就会成为世界康德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汉语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相对于“中国哲学”之名而再造一个“汉语哲学”之名,是从哲学现象自身特性出发“取实予名”的结果,也是哲学研究的专业性要求基于常识和日常语言,而又超越常识和日常语言的创新选择。
人类的语言各异,但有共享的哲学问题
前述三位学者在讨论“汉语哲学”时,都谈到了“普遍性”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人担心提倡“汉语哲学”,可能会导致对普遍性哲学问题的忽视,将哲学局限在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之中。因此,他们分别提出了如何处理汉语哲学的特殊性、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张力问题的方法。但笔者的想法是:虽然哲学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加以表述,但哲学有共享的问题。发源于古希腊的关于存在(Being)的哲学问题,是古希腊语言中的特殊哲学问题。此一特殊的哲学问题与古代“汉语哲学”中关于天道、道、有无的特殊哲学问题,具有可沟通性。可见,不同的区域、国别有共享的“形而上”哲学问题,但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形而上”问题的内容,是可以不同的。
人类从古至今都共享着一些普遍的哲学问题,如善恶、和平、正义、幸福、平等、自由、权利等关乎人类是否能够达致美好生活的问题。人类从各自国别、区域的生存经验出发,对这些人类共享的问题给出了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回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比古人更加有利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条件下,有着更加开阔的文明视野来考察人类基于不同生存经验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因而能够以更加多元的哲学视角来重新审视思想史上人类共享的问题,并尝试提出更加合理、周延的哲学论述。
强调“共享的哲学问题”,并肯定不同民族语言的哲学论述思路,进而丰富我们人类对于共享哲学问题的认识,这是我们提出“汉语哲学”,并坚持汉语哲学、发展汉语哲学的主要依据。这也意味着,我们提倡、坚持、发展汉语哲学,并不会忽视其他民族、语言的哲学,而是希望通过“汉语哲学”的观念唤醒当今世界不同民族语言哲学的自觉,让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从自己的生存经验出发,用自己民族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对人类的共同问题给出智慧性的哲学回答,进而让多样的文明经验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丰富人类的智慧宝库。
总之,笔者给出的结论是: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捍卫常识的“汉语哲学”。通过常识的汉语哲学可以展开不同形式、深浅不一的汉语哲学的专业讨论,以发展汉语哲学,发展中国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的汉语哲学透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09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