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何川(中国盲文图书馆副馆长、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
编者按
对一般人而言,阅读是十分平常自然的事情,可对我国1700多万视力障碍人士而言,阅读却是那样的得之不易。本文是一位两岁就失明的视障者关于自己阅读经历的深情讲述。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视障人群对于阅读的强烈渴望,也可以看到我国无障碍阅读事业的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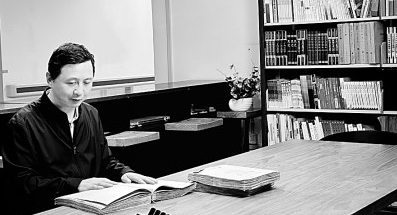
本文作者何川在阅读盲文图书。照片由作者提供。
两百多年前,法国的布莱尔发明了盲文,后来它逐渐成为全世界失明者的文字。
20世纪80年代,我进入盲校学习。在老师的辅导下,我纤细的指尖第一次触摸到盲文那神奇的凸点。那一刻,一颗星星在我的世界悄然点亮,那是一个盲孩子的鸿蒙初开——我的阅读生活由此开启。
我通过盲文学习语数英,也学理化生、史地政。但是,几十年前的盲文图书还不够丰富,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少数课外读物,可供阅读的盲文图书非常有限。
1991年,我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要想顺利完成学业,必须大量阅读。可当时,无论课内用书还是课外读物,盲文版都比较缺乏。面对书荒,心里更慌。我和同学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以琴换书。我们在校园里四处张贴启事:谁愿意帮我们读书,我们可以教他(她)弹吉他。这个办法很管用,每天都有许多同学排队来帮我们读书。我用录音机把同学们读的书录下来,空闲时一遍又一遍地听。202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回了一趟母校。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物是人非,但当年读书的场景,我依然记忆清晰,甚至还能随口背出当年同学们给我读的《百年孤独》的开场段落以及《简·爱》中的经典告白。
通过这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大学期间我读了很多书,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我入职中国盲文出版社,从一个阅读者成为一名盲文编辑,专门从事盲文出版工作。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盲文出版的历程。
1953年7月,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组建盲文编译组,同年,《新盲字方案》在全国推行,盲文出版有了统一标准和规范。此外,中国盲人福利会也在1953年成立,内设盲文出版组,这是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前身。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盲文图书《谁是最可爱的人》出版发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一代又一代盲文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盲文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盲文图书纸张用料特殊,制作过程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从前期调研到选题策划,从校对到印刷,一部盲文图书的面世往往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之久。仅靠有限的盲文图书远远满足不了广大盲人读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
20世纪90年代末,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已开始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也正是在那时候,我打听到清华大学茅于杭教授研制出中文世界第一款读屏软件——《清华双星》,盲人借助它可以简单操作电脑。1998年夏天,我买了一台电脑,并在茅教授的指导下学会使用读屏软件。那个夏天,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因为通过读屏软件,我可以阅读我喜欢的任何书籍——我的阅读从未如此自由。接下来好几年,我一直沉浸在这种阅读的快乐中。
要让更多盲人朋友享受到这种阅读的快乐,就需要解决盲文出版自动化问题。2001年,为解决该问题,中国盲文出版社专门成立了一个软件开发小组。由于我掌握电脑的基本操作技能,而且对读屏软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被选入软件开发小组。从此,我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历程。我们的软件开发成功后,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阳光》,它可以辅助视障人士使用电脑,也可以用于印制盲文文件、材料、书刊等。从此,更多视障人士在阅读便利性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青海有一位盲人医生,叫任志平。他从小酷爱读书,只要一有空,便请周围的朋友帮他念书,但这种方式始终不能满足他旺盛的阅读需求。
一天深夜,我家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惊醒后一阵心悸,惊慌中拿起电话。
“喂,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电话里传来任志平无比激动的声音。
我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耐着性子听。
“我活了70多岁,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幸福,因为我借助《阳光》软件能在电脑上读书了!我现在想什么时候读书就什么时候读,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你能理解我的这种幸福吗?”
那天,任志平在电话里还说,这幸福来得太晚,他已经70多岁了,要是早一点就好了!
电脑和读屏软件再加上互联网,让盲人可以实现阅读自由,但这对许多盲人而言成本还是有点高。2005年,我提出研发“盲人听书机”。利用当时已经成熟的TTS(文字转语音)技术将电子文本图书用机器语音方式朗读出来。产品一经问世便受到许多盲人读者的青睐。作为一个常年保持阅读习惯的人,我的阅读也因此更加便利了。无论是在出差途中的火车和飞机上,还是在入住的宾馆里,我都可以借助“盲人听书机”随时随地自由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中国残联原主席张海迪说:“盲人文化事业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要尽可能地消除现代化生活给盲人带来的信息障碍,让盲人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学习和阅读,了解生活,获得信息,学习技能,最终融入社会。”为破解盲人读书难、买书难、藏书难的问题,1994年,中国盲文图书馆成立,2011年6月,中国盲文图书馆新馆开馆。
中国盲文图书馆新馆开馆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图书馆各类文化活动多姿多彩,阅读推广如火如荼,无障碍电影绘声绘色,志愿服务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盲人读者走进盲文图书馆,他们在这里感受现代文明,触摸世界脉搏。今天的中国盲文图书馆,已经成为全国盲人的文化、科技、教育资源中心和知识服务中心,成为向公众开展人道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而我,也从一名热爱阅读的读者变成一名图书馆员,从一个读书人变身为一个讲书人、荐书人。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跑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组织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我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盲人爱上了阅读,盲人群体主动接受文化服务的意愿不断上升。
从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盲人文化事业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突破都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盲人文化工作者安贫乐道、甘于奉献的坚守,更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残疾人事业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
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持续增加对残疾人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保障力度、提升保障水平。
2017年,中宣部等五部委共同启动“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20万台智能听书机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向广大盲人读者免费出借。足不出户的盲人朋友,通过连接互联网的智能听书机,可以免费获取海量优质悦听资源。这意味着盲人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
2018年6月,《国家通用盲文方案》正式颁布,从此我们有了更规范、更精确、更好读的盲文。
2022年5月5日,《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这是版权领域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人权条约。未来,盲人阅读将在版权方面获得更多支持,每个盲人的阅读需求都将被看见、被重视、被满足。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从无障碍的角度为支持盲人阅读提供了法律保障。
虽然我两岁就已失明,但通过阅读,我习得了知识,淬炼了思想,提升了修养,从而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这个我无法用眼睛看清的世界。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投入的不断加大、制度和法律保障的不断健全以及社会各界的持续支持,视障人群的阅读障碍将被一一清除,每一位盲人朋友都可以像我一样,通过阅读点亮自己的世界。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3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