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编书者说】
作者: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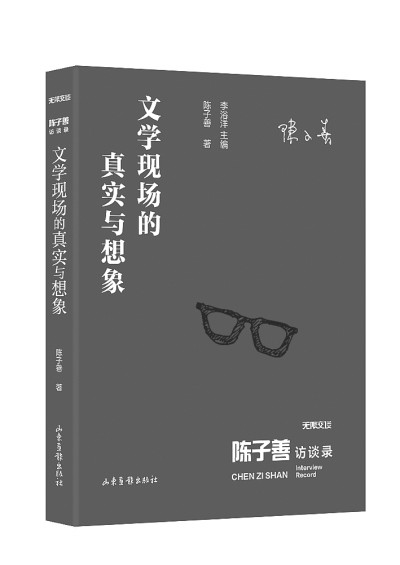
《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陈子善访谈录》
陈子善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访谈、对话、口述其实古已有之,并非现代事物,典籍中的各类“答问”“语录”“口说”便是。但进入现代以来,传媒大兴,置身其中,使得本以著书立说为职志的文人学者还需要能言善辩,最好出口成章、对答如流。与之对应,访谈文体开始异军突起,到了近年更是成为时尚。这不仅是对于媒介环境的回应,亦是新的传播与接受习惯使然。试问,谁没读过几篇访谈,或者看过几档访谈节目?
当然,因为访问者与受访者的身份都有多种,访谈也有不同类型。具体到文人学者的访谈,在我看来其不只是一种别致的文体,往往也有独到的内容。与体系严密的著作相比,访谈可以讲述幕后的花絮、揭示背后的关怀,也可以记录丰富的体验、表达思考的延伸。好的访谈与好的著作相得益彰,好的访谈也和好的访谈对象相互成就。从访谈中,既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观点,更能够看到这个“人”本身。
有鉴于斯,我策划主编了“无限交谈丛书”,首批出版四种。丛书定位“一人一书,一书一题”,“希望在保留文体的生动性与开放性的前提下,还能凸显其治学、深思的主要成果与最大特色”。四位作者皆为文学研究名家,各有擅长,并且著作颇多。“访谈也许只是‘补白’”,却“能够把背后的真性情、真忧患与真关怀和盘托出”。
但话说回来,时代固然期待文人学者出口成章、对答如流,真正精于此道的其实不多。这四位学者皆在此列,而每年“上海书展”的“劳模”陈子善先生更属典型。他出场次数多,发言效果好,知识面广,互动性强,而且善于说故事,关键时刻有“金句”。这些都决定了他是理想的访谈对象。“无限交谈丛书”中的《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陈子善访谈录》是其访谈文字首次结集,伴着他高辨识度的沪上“腔调”华丽亮相。
所谓陈子善的“腔调”,首先是指他的一口“沪普”。听陈子善讲话的人一定印象深刻,以至再读他的文字时,仿佛带有回响。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其访谈内容极具个人特点。访谈录分为四辑:“谈文学史观”“谈现当代作家作品”“谈学术追求”与“谈阅读体验”,凡22篇。篇名中的关键词提示了陈子善的主要兴趣与贡献——“历史”“碎片”“失踪者”“手稿”“阅读”与“书”。此中的主角无他,唯有“书”。各篇或因书起,或落为书。要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要么是陈子善自己的旧作新书。而陈子善谈论的“书”,一定都是经他发现、整理、鉴别甚至抢救的“书”。一切围绕“书”,这是陈子善“腔调”的核心。
陈子善老师在学界内外以治现代文学文献闻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创办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编《现代中文学刊》期间也将该刊经营成为发布与研究现代文学文献的重镇,与北京老牌的《新文学史料》交相辉映。此外,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著书、编书不辍。尤其是他编选的几十种文集,绝大多数是首次结集,文献意义显著。不少作家作品因为他的工作而重见天日,他也因此被誉为“移动的图书馆”——或许“文学史的勘探师”更为准确,毕竟“图书馆”有界而“文学史”无边。陈子善最新一本著作的书名颇能显示其自我定位——《在文学史深处打捞》。
在《在文学史深处打捞》的推荐语中,我写道:“文学史研究走向纵深,离不开理论视野的照亮与叙述方式的更新,但更离不开具体史料的支撑。陈子善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置身现代文学史料发掘、考辨与阐释的前沿。而史料前沿正是最接近历史现场的地方。他以不懈的积累与求索,缀合出了一幅更为整全、立体与多元的文学史图景。这是‘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三十余年来的一份厚重的‘实绩’,也承载了一位当代人文学者的担当。”如果结合《陈子善访谈录》中篇幅最长的两篇自述学术历程的访谈《钩沉辑佚,以小见大》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则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由于十分鲜明的工作内容与个人风格,陈子善在文献史料方面的功夫受到屡屡称赞。不过我以为与文献史料本身相比,他谈“文”论“学”,根柢其实在背后的“人”。如果没有人的温度,文献史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陈子善与钱理群先生合作主编过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学者提出“文学史”的主体是“个人文学生命史”,也就是说,一次发表、一个版本、一段争鸣、一种实验……背后无不关联具体的人的生命瞬间。陈子善的研究正是秉持了这样的理念。其入手处通常是“物”,但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人”。而对于那些把“物”与“人”联结起来的部分,比如作家手稿、编辑行为、签名本与回忆录,尤其用力。说到底,他关心“书”的命运,但更加关心与之相关的“人”的命运。
陈子善关心“人”,里面有他对于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中经历的体贴与同情,有他对于人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的好奇心,还有他本人对于人道主义的执着坚守。也只有把时常仗义执言的他与那个“好玩”的他合而观之,才是完整的陈子善。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他那些专业又非常具体的工作才和我们有关。概言之,他的确自得其乐,但不是自娱自乐;他做的确实多是一些“小”题目,但却并不“轻”;他在文章、演讲与访谈中展开的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片段,但无数个片段缀合起来,就是一幅充满人性光辉的长卷。陈子善在访谈中说:“我从不怀疑我的工作。”我想,他的信心和底气就在“人”的魅力。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03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