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张同胜、谢林(分别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学人小传
王宁,1955年出生,江苏扬州人。197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留校任教。1989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到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1997年到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任教,2001年任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曾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等。
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青年教师王宁初入学术界,就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20世纪末国际文学理论的天空上,密布着“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愁云;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正在面临“失语症”。怀着一腔赤诚与一往无前的历史使命感,王宁立志改变这样的困境。
40多年后,作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王宁,一如青年时代那样,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累累硕果,期待站在新的起点再次扬帆远航,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实桥梁。他常引用那句古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走上学术道路
王宁1955年生于南京,初中时跟随父亲到盱眙生活。他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尽管那时能看到的书不多,但他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林海雪原》《牛虻》《高老头》《双城记》等几十本中外名著。这些名著无疑对王宁走上学术道路产生了影响,也为他日后从事西方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础。正如他后来所说:“不读几百部文学作品,你不可能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你不可能去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1978年,王宁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留校任教,同时在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担任外国文学教师。那段时间,他不仅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和许多文学史书籍,还接触到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学术积累渐深,他的工作重心从英语教学转到了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王宁最初的研究领域是“英美文学”,特别是20世纪的美国文学。他钟情于海明威的著作,他的个性也与海明威有些相似,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取得杰出的成就,不然宁愿放弃这项工作。年轻时的王宁兴趣广泛,曾经是学校足球队的后卫,后来又迷上了乐器,能演奏二胡、笛子、小提琴,但为了全身心投入学术工作,他不得不把这些从小养成的爱好一一放弃。也正是这样的专注,才使得王宁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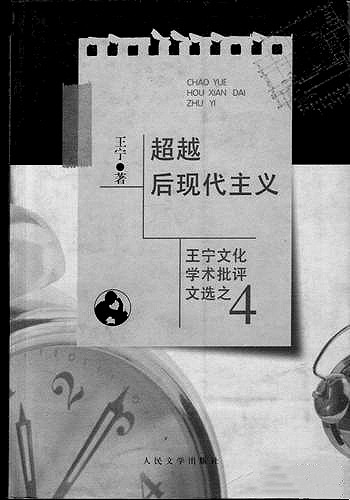
1986年,王宁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师从著名学者杨周翰攻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杨周翰治学严谨,对学生很严格,王宁每次去见老师,都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生怕被问倒。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他啃了不少英文理论原著。有一次,王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受到与会学者的肯定,他有些得意,可杨周翰读过论文之后对他说:“看来你的英文写作还要大大加强啊!”“你不要因为受到国外学者的几句赞扬就沾沾自喜起来。要知道,那些老外是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看待中国的青年学生的,他们知道学习一门外语的困难,因此在他们看来,你这样的中国青年学者能熟练地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并写成学术论文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但你自己千万不能满足啊!”那次交谈后,王宁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英文的学术写作上狠下功夫。杨周翰严谨的治学风格、朴实的生活作风都深深影响了王宁,王宁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与教学风格——专注、严谨、认真、勤奋。如今,提及恩师,王宁说:“他的帮助令我受益终生,所以我也要继续传承这份教书育人之魂。”
学生时代深厚的学术积累,为王宁日后的学术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足鼎立与世界诗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宁在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及西方文论引进、外国优秀文学作品译介等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成果。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面对“世界文学”研究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对比较文学学科造成的困惑与挑战,王宁提出了“世界诗学”的构想。
在王宁看来,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形成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时至今日,很多人在谈到外语时,首先想到的是英语,在谈到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时,首先想到的是欧美文学。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受到极大启发。同样,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建构产生过较大影响,只不过绝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对此全然不知,或拒不承认。今天,在世界文学已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的情况下,文学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使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一些理论话语步入前台,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研究者可以在同一层次进行平等对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建构一种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的世界诗学。王宁主张,突破长期以来一直主导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调整东西方文化关系上的“逆差”现象,提倡世界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
如何使得中国文化理论研究与西方文化理论研究“平起平坐”?王宁在借鉴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等学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欧洲学派”“北美学派”“东方学派”三足鼎立的比较文学研究新格局。其中,“欧洲学派”以实证主义社会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为研究背景,以法国为中心;“北美学派”注重平行研究与诠释学传统,以美国为中心;“东方学派”进行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文化平行比较研究,并且兼顾“影响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以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中心。“三足鼎立”理论的提出,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为实现东西方文论、文化研究的平等对话,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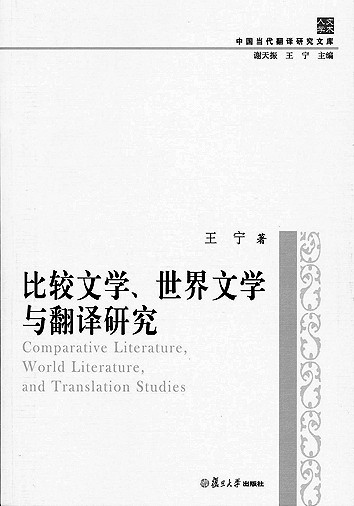
王宁时常会想起杨周翰先生对学生们的嘱托:“我的这些‘老古董’就不要去重复了,去重新开拓一个新领域。”在提出“世界诗学”构想时,王宁着重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构建“世界诗学”时,首先需要对中国和西方以及东方其他主要国家的诗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否则就是重复前人或外国人已做过的事情,而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世界诗学”并不是以一个相同的审美标准来对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学进行理论构建,而是基于一种相对普遍的审美标准所进行的理论构建。王宁为这个理论的构建设定了多个标准: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于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可以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现象;做到普遍性与相对性结合,尤其是要注意使其具有理论的开放性;在运用于文学阐释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的阐释”,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进行对话,并对人文学科理论话语的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它具有可译性,有助于对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一种理论只要能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就可跻身世界诗学,其生命力也在这种未完成状态中体现出来;每一时代的文学理论家都可在自己的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中,对世界诗学理论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
王宁对“世界诗学”标准的界定,表明他对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发出“中国声音”的决心,体现出他作为中国学人的责任与担当,也体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性。王宁希望,每一个时代的研究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研究实践所产生的学术成果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世界诗学”,将“世界诗学”发展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化理论。
时雨春风育桃李
“只要看准一个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即使经历失败和挫折也绝不回头。”一项项创新成果的背后,是王宁永不停歇探寻真理的恒心,为了学问,他有一种摩顶放踵的劲头。
王宁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生安锋回忆:在清华大学工作时,老师每天早七点都会准时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来到清华园文南楼展开一天的研究与教学,中午一般在学校食堂吃饭,通常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只要不出差,他永远都在办公室。几乎每天都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年年如此。王宁对学术始终保持着最热烈的爱,兢兢业业,坚定执着,生安锋及一大批青年学者都以他为治学、做人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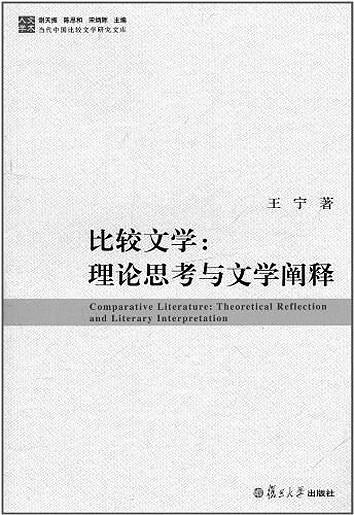
王宁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执教四十余年,无论研究工作多繁重,他都坚持为本科生授课,细心指导硕士生与博士生的论文,和学生们反复推敲选题。王宁从不限制学生的论文选题,常常鼓励他们独立思考,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与各类项目,培养全面能力。如今,王宁培养的青年学子们已经成长为许多名校比较文学、翻译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的中流砥柱。每每提及王宁,他们总是会想起老师的平易、执着和宽容,也会回想起老师在学术上的严厉,感恩他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
王宁一向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他不仅爱护自己的学生,对其他年轻学者同样爱护有加。只要有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地给予指导。因此,虽然许多青年学者没有正式成为王宁的学生,但也将他视为自己的老师,按照王宁指引的方向走上了学术道路。
王宁给学生传授做学问的经验,更常常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中国学者?王宁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家国情怀,要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安锋曾写道:“王老师还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富有家国情怀,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传播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在学术上,他更是身体力行,从早年起就注重借助自身的外语优势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优秀的中国文艺作品。他不但自己著书撰文评介现当代中国文学,将很多中国作品译介到国外,而且多次借助自己的声望与国际知名期刊合作,发表中国学者的文章,向国外学术界介绍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正如生安锋所言,王宁作为一位立志将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的中国学人,深知学术研究绝不可闭门造车。多年来,王宁一直致力于参加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各类交流活动。王宁的学生、北京科技大学讲师李琳写道:“王宁一向重视与学术界同行的学术联系,与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学术交往。一方面,他积极走出国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讲学,代表中国学界在世界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地将国际上的学术大师请进中国,与国内学者展开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

王宁(右)在学术会议上。
除了积极将中国学界的声音带向世界舞台,王宁也在不断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努力着。1997年,王宁离开北京大学前往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正式展开该校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经过艰苦奋斗,北京语言大学于1998年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又于两年后获得了博士授予点。在王宁的带领下,北京语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学术水平逐年提升。这场“战役”刚刚告一段落,王宁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调入尚在建设阶段的清华大学外语系。仅仅三年后,清华大学外语系成功申请到了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短短几年内将该博士点建成北京市重点学科,并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点。与此同时,王宁为了延续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又在清华大学创建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由此推动了清华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
“金科玉律真师范,化雨春风入我庐。”治学近半个世纪,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王宁仍然坚定地走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在世界舞台讲述中国学问,培养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学人,是他不懈的追求。
学人论学
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当下谈论含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早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人们或许会认为,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江河日下的情形下,文学面临死亡境地,谈论比较诗学还有何意义?这种讨论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只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并不代表整个世界的文学理论状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通过近百年来学习西方理论和弘扬比较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娴熟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此外,我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现在已到了建构中国的理论话语的时候了。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化千姿百态,能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审美标准吗?我认为:在绝对意义上说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依循一种相对普遍的审美标准来进行理论建构还是可以做到的。对此,可从“世界文学”理念的建构中见出端倪。当年歌德提出这一构想时,几乎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假想,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歌德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但他同时又陷入了德意志中心主义的陷阱。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提到“世界的文学”概念,才将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联系起来。后来,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世界主义的理念被放逐到边缘,尽管一些有着比较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文学研究者大力提倡比较文学研究,但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依然缺乏一个整体的和世界文学的视野。
需要强调的是,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也能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关于前者,我们可从最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出现的“重建中国批评话语”的尝试中见出端倪。张江在质疑西方文论时已大胆提出自己的“本体阐释”构想。由此可进一步推进,仅用现有的理论进行文学阐释并不是理论工作者的最终目的,关键是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这样才能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各种理论话语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开始时会比较微弱,甚至完全有可能为国际学界所不屑。但是,随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的日益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论的地位也会相应得到提高,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不言而喻,当下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的努力仍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中国文学究竟有多少作品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去很少,现在已开始逐步增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这一现状与中国文学的实际很不相称。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诗学的建构对于重写世界文学史,进而扩大中国文学和理论在世界文学和文论版图上的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和非常有益的原因。关于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已故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曾提供颇有说服力的例证。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推动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进程还有待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如果说,歌德当年呼唤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确有点不合时宜,那么,在今天世界文学已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的情况下,世界诗学的建构将不会遥远。
——摘编自王宁《世界诗学的构想》,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