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乔忠延(山西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一曲合唱,却生发胜过机枪、大炮、飞机的精神力量,成为唤醒民族斗志的利刃。时光远去,旋律永存。聆听黄河浪涛,翻检图书资料,无处不激荡着《黄河大合唱》的铿锵诗意,无处不传颂着《黄河大合唱》的磅礴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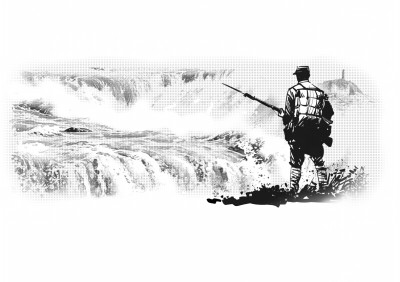
插图:郭红松
“这次我们来个大的”
1939年1月,延安边区医院。灯光下,何穆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两位大夫正在给一位伤者做接骨手术。
这位伤者,就是后来因《黄河大合唱》闻名全中国的光未然。那时他身兼三职,既是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以下简称“演剧三队”)的领队,又是该队的特别支部书记,还是“军委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受伤前,光未然带着演剧三队在吕梁山的抗日前线演出。几日前,在山西汾西翻越山壑,战马受惊,他栽下马来,摔断了左臂。战友们护送躺在担架上的光未然渡过黄河,又跋涉数百里,把光未然送进延安边区医院。
到了延安,光未然的伤痛还在加剧。医院条件简陋,没有麻药,正骨复位要硬生生拽开错位后粘连的伤口,再慢慢对接。火焰炙烤般的疼痛变成了烈火焚烧般的剧痛。
病床前,出现了一个令光未然异常惊喜的面孔。冼星海来了!与多次联袂创作抗日歌曲的搭档不期而遇,光未然一下忘却了疼痛。光未然与冼星海相识于上海。一天,光未然来到了上海救亡歌咏大会。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有人教唱歌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震天的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听到这首《五月的鲜花》,光未然激动万分。这首歌是他为自己的剧本《阿银姑娘》所写的序曲,没想到会在上海传唱。光未然正回想在武汉满怀悲愤创作的情景,来自北平的诗人李雷看见了他,大声喊着“词作者光未然来了”,就把他推上了主席台。教唱的人立即握住他的手,并自我介绍:“鄙人冼星海。”
光未然也久闻冼星海的大名。《流民三千万》《我们要抵抗》《战歌》《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冼星海创作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顿时萦绕在光未然耳边。不几日,他们共同创作了《高尔基纪念歌》。日寇进攻上海,抗战文化团体撤退到武汉。在长江边,光未然与冼星海连续合作,一起完成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10首歌曲。在武汉时,他俩同住一间屋子。冼星海常会把睡着的光未然唤醒,哼出曲调,催着他赶紧填歌词。
武汉一别,二人各自奔赴抗战前线,光未然哪里想到竟然会与冼星海在延安重逢。此时的光未然,已经历了抗战烽火的淬炼。见到冼星海,他便将胸中的抗日烈焰喷涌出来。冼星海明白了,光未然是要写一首长诗。冼星海坐不住了,蓦然站起,说:“写,这次我们来个大的!”
“对,来个大的!”
如何才能格局大、气魄大、威力大?光未然将身体的剧烈疼痛,化作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焰。他的儿子张安戈在《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中写道:“父亲运用大合唱的结构,以黄河作为主体,贯穿整个作品。他以黄河的历史,黄河对民族的哺育,黄河的屈辱,黄河的呻吟,黄河的觉醒,黄河的怒吼为载体,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意志……悠长的叙事,民谣的流淌,淳朴的乡音和悲愤的哭诉,在最后变成了礼花一般爆炸性绽放。”
一连数日,光未然或踱步,或倚床,唇齿间激扬着感天动地的巨澜。演剧三队派来照料他的队员胡志涛奋笔疾书,记下每一个字词。她哪里会料到,手下笔录的竟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鸿篇巨制!
行船好比上火线
“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那是1938年11月1日,南国还是庭院花木深的秋景,北国却已是草枯水已寒的初冬。日寇妄图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撕开口子,打过黄河。日寇一次次疯狂扑来,又一次次被打得滚下山去。
战场还未到,渡河已拉开惊心动魄的序幕。如何惊心动魄?听听《黄河船夫曲》:“乌云啊,遮满天!波涛啊,高如山!冷风啊,扑上脸!浪花啊,打进船!”稍有不慎就有船翻人亡、葬身鱼腹的危险。怎么办?冲上前!“伙伴啊,睁开眼!舵手啊,把住腕!当心啊,别偷懒!拼命啊,莫胆寒!不怕那千丈波浪高如山!不怕那千丈波浪高如山!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行船好比上火线”,我完全理解光未然那一刻的心情。1994年,我曾在山西吉县体验黄河漂流。船夫一解缆绳,我即落入心惊肉跳的险境。岸上看着如鱼鳞般柔和的细浪,此刻竟然“高如山”,危若峰,随时可能倾轧下来,把我们砸个粉身碎骨。胆寒,令人胆寒。心惊肉跳的我抓紧座椅,一刻也不敢松手。莫非这就是黄河对我的教诲,让我更深入理解《黄河船夫曲》?
时任演剧三队音乐组长、《黄河大合唱》延安首演指挥的邬析零,曾撰文描述东渡黄河的惊险场面:“40来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船头挺立着一位60来岁的白胡子老人。10来分钟后,渡船已至大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浪花汹涌地扑进船来。那位白胡子老人直起了脖子,喊出一阵悠长而高亢、嘹亮得像警报似的声音……”
光未然将白胡子老人的高亢呼喊,淬炼成了诗句:“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从陕西宜川的圪针滩坐船,到对岸山西吉县的小船窝登陆,黄河给演剧三队的同仁们上了惊心动魄的第一课。他们跳下船,爬上河滩的巨石,拍下了挺进河东抗日战区的首张合影。不是他们征服了黄河,而是黄河用惊心动魄的巨浪荡涤了他们的内心。
登上岸边的大路,演剧三队的同仁们忽然听见了山呼海啸般的声浪。这些血脉里流淌着音乐文化细胞的艺术尖兵,肯定会将这响声与刚刚经历的那惊心动魄的黄河巨浪联系在一起。可是,左右环顾,总是看不见发出声浪的地方。比声浪更为直观的是黄河的水雾,或者说,是水雾暴露了轰鸣声浪的场所。
这就是黄河壶口,传说中大禹治水的第一站。大禹带领先民劈开石槽,打通淤塞的河道,洪水奔流直下,黄河便拥有了壶口这世所罕见的瀑布。
壶口,气势非凡的瀑布,百看不厌的瀑布。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上游宽阔的河道里舒展肢体,奔波欢跃,猛然遭遇了几十米深的断崖河槽,一头栽跌下去,顷刻粉身碎骨,水雾喷出河槽10多米高。那声浪仿佛粉身碎骨的呐喊,那水雾就如粉身碎骨的飞溅。
那气势不是排山倒海,胜过排山倒海;不是天崩地裂,胜似天崩地裂。我观赏过20多次壶口瀑布,每次都冲动得直想高喊:黄河在咆哮,黄河在怒吼!
看看光未然怎样走笔:“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这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二节《黄河颂》。
谁愿意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这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保卫黄河》。何等壮怀激烈,何等斗志昂扬!这昂扬的斗志从何而来?临汾的山川写着最佳答卷。随着旋律唱出这雄壮的气势,我似乎看见了光未然一行,从河东的乡宁县,经过吉县、蒲县,到达了隰县的午城镇。
他们的歌声、短剧,闹沸了这个山区小镇。乡亲们都来领受这久旱逢甘霖的精神慰藉。最后一个节目落幕,乡亲们簇拥上前,不仅用午城镇特产的蜜汁金梨慰问演员,还兴奋地讲述歼灭鬼子的故事。
在临汾市的党史资料中,我查考到了乡亲们所讲的故事。1938年2月28日,日军侵占临汾城后,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在山西北部,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大捷,日寇遭受重创。但是,日寇仍向南进犯,攻占晋南重镇临汾。不几日,日军第二十师团西渡汾河,侵占蒲县和大宁县城。
日寇盘算着,似乎如此推进,很快就会夺得黄河渡口,很快就会跨过天堑,窜入陕北。日寇增兵几日推进无阻,一路西侵,横行霸道。
其实,日寇已经中了我军的骄敌之计。3月17日,日军几十辆满载各种物资的汽车、6辆拉着步兵的卡车,出蒲县城得意扬扬西进。行至井沟和午城地带,钻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我军枪弹齐发,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日寇残部丢下满地尸体,仓皇逃进近在咫尺的午城。夜晚,我军关门打狗,歼灭了龟缩其中的全部日寇。
次日,恼羞成怒的日寇派兵卷土重来。此时,游击在附近的八路军部队,早已张开一个大口袋。待日寇赶到,扎紧首尾进出口,从两侧山头居高临下,集中火力猛攻。日寇不但未能西渡黄河,而且全部命归西天。史料显示,此役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还有大批军用物资。
在屈辱中悲伤,在悲伤中涅槃。黄河儿女挺起钢铁般的脊梁,拿起武器,誓死反抗侵略者。胜利的捷报掩压住光未然骨骼的疼痛,条条筋脉燃烧起冲天的烈焰,光未然像壶口瀑布那般倾倒心胸的激浪:“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般地壮烈!”
胡志涛紧张地用笔记下歌词,手写累了,也不敢停歇。稍一迟缓,就会被那词语的浪潮甩开好远,不得不喘息着追赶前去。5天,整整5天,终于写下:“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她画出这个惊叹号,等着光未然继续口授。来回踱步的光未然却没有发声,轻轻坐在了椅子上。胡志涛问:“完了?”
“完了。”
胡志涛站起来咯咯咯笑着说:“不是完了,是好了,太好了!”
怒吼吧,黄河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1939年3月11日晚上,冼星海和演剧三队的全体人员,集聚在延安西北旅社一间相对宽阔的窑洞里,大家围坐成一圈。
左臂打着绷带的光未然站在中间的油灯旁,简短的几句介绍后,禁不住心中蓬勃的激情,放声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朗诵到“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时,油灯似乎不亮了,人人眼中放射着光芒。朗诵到“老家已经太不成话了!谁没有妻子儿女。谁能忍受敌人的欺凌”时,有人想到千里以外的父母兄弟,禁不住涕泪交加。光未然的语速越来越快,犹如雷霆轰鸣:“怒吼吧,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已经团结起来,誓死同把国土保……”
光未然朗诵的尾音还在回荡,滚雷般的掌声已经响起。掌声未落,“冼星海霍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张安戈《我的父亲和〈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没有急于动笔,每天泡在演剧三队,聆听队员们讲述奔赴河东山川的经历和感受。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射到延安城东北的桥儿沟,那里坐落着鲁迅艺术学院。山坡上的一间小窑洞,连续6夜都亮着灯,冼星海就在那灯光下哼哼唱唱,写写画画。冼星海写写画画的稿纸,是粗糙的土纸,好在贤内助钱韵玲已经在上面画好了带有简谱小节线的格子。
写到深夜,只要冼星海不睡,钱韵玲便相依相伴。觉察到冼星海有点困了,她就用黄豆炒煳的粉末冲杯“咖啡”为他提神;发现他有点累了,她就拿几颗红枣煮一煮给他补气。
夜已深,冼星海仍旧兴致盎然,丝毫没有搁笔的迹象。陕北的三月春寒似严冬,夜里尤其冷冽。备用的木炭不足,火盆里微弱的火苗燃尽最后的炭屑,瘫倒在灰烬中熄灭了。
时间已至凌晨,激情澎湃的作曲家却无心入睡,还在奋笔疾书。钱韵玲便递过糖瓶,冼星海小心翼翼地挖一小勺白糖,送进嘴里。瞬间,口舌的甜蜜催化出周身的温热,大脑灵光迸发;瞬间这灵光已化作美妙的乐曲,从笔尖流淌到纸面。
油灯明灭,6天6夜,冼星海终于在怒吼的歌唱声中撂下了手里的笔,小桌上厚厚摞起68页曲谱。
1939年3月31日,冼星海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全部8个乐章。
燃遍了抗日的烽火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大幕拉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乐器有些寒酸,除了吉他、小提琴两件洋乐器,其余都是本地找来的,竹笛、大鼓、梆子,还有木鱼。连煤油桶和搪瓷茶缸也搬上了舞台——煤油桶被改造成了低音胡琴,搪瓷茶缸里放进了十几个小铁勺。看看礼堂中座无虚席,有人叹息,这么寒酸的乐器,对得起观众吗?
对得起,对得起!
演出开始,搪瓷茶缸里的10多个铁勺摇动开来,哗啦哗啦的金属撞击声,与管弦、锣鼓一起模拟出了黄河浪涛声。接着,响起天崩地裂的喊声:“咳哟!划哟!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咳哟!咳哟!”
全场肃静,人人瞪大眼睛,都沉浸在气势恢宏的合唱中,脉搏疾速跳动,胸膛急剧起伏。有人和着节拍悄悄挥臂,有人随着吼声暗暗踏足,大礼堂沸腾了。
演出时,在沸腾!
谢幕了,还在沸腾!
自此,延河畔到处飞扬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
自此,“松花江在呼号,黑龙江在呼号,珠江发出了英勇的叫嚣,扬子江上燃遍了抗日的烽火!”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