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当代性与敞开的“百年中国文学”
——读《现代的形成与拓路》
作者:李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如何从整体上评价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这是文学史难题,更是理论难题。它需要将“百年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探索性空间,一种活的资源。陈晓明主编的《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一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为“百年中国文学”找到的立足点是“当代文化建设”,这指向了一种传统的生成和创造。“百年中国文学”成为一种敞开的存在,一种具有未来性的历史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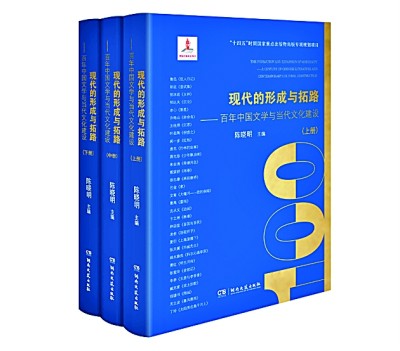
理论上的“当代”,是“当代性”展开的过程。“当代性”一词并未出现在《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的书名和导论中,但却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基础。在编写该书期间,陈晓明专门探讨了文学的“当代性”问题(《论文学的“当代性”》)。他指出,在西方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当代”或名词化的“当代性”(contemporaneity)是可以与“现代”(modern)或“现代性”同义的,它属于现代的一部分,或者是现代的另一种表述。汉语中的“当代”“当代性”,时代意识的意味很明显,“意指说话主体对我们经历的这一时段的一种整体性把握,它包含了这一时段特殊的存在感,也表达了一种哲学上的现实感。”“‘当代’所包含的特定的和复杂的含义是西方或‘世界’所没有的,在文学史方面的使用尤其如此。它不只是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还包含着对一个特定时段的命名,赋予它一种质的含义;并且通过这个命名,即通过确立‘当代’的意义与外延,再返身确立‘现代’的意义。尽管在欧美文学史的表述中,也可能出现‘当代’,但这个‘当代’是时效非常短的‘当下’或当前,或最近十多年发生的事情。”总体来看,“‘当代性’是文学艺术作品整体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蕴含,它是在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建构起来的认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副标题的“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并非两个文学史对象的并置,而是一种新的认识关系的建构——从当代出发,打开“现代中国文学”。主标题中的“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不是线性展开的历时性过程,更像是多面敞开的共时性结构。
在《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中,百年中国文学向“当代”敞开了六大面向:传统、世界性、大众化、伦理、民间、新媒体。这六个面向,并非拼凑在一起的六块版图抑或六种特征,而是六种互通的进路。从文学史论的角度看,该书没有把百年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封闭的“六面体”,而是“六面镜”,它们不仅映照出历史,也向所有在大地上凝视着它的当代人敞开,向着有无数可能性的未来敞开。也正因为如此,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例如文学、革命、人、时代等,会在不同的章节出现,但每次出现的侧重和背后引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与其说是在论述“百年中国文学”的不同面向,不如说是在用尽可能多的当代性的镜子,帮助人们看清何为“百年文学”“现代中国”。
这些敞开的面向,几乎涵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全部的重要命题。这些命题在漫长的学科化过程中,不少都被封存为常识了。此时,那种对话、反思的“当代性”,也就消逝了。在《现代的形成与拓路》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常识,被划分到六大面向中重审。这不是在肢解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本体”,将其“散作满天星”,而是通过六种面向重筑历史坐标,形成新的“星丛”,照亮当代夜空。随手翻看《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的章节,能获得一条“百年文学议题”的线索,它具有索引作用,但若把多个章节进行组合、参照阅读,则能得到更多鲜活的理论启示。例如,该书第三编的“大众化面向”,讨论的是百年文学中的文化人民性问题,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延续到了当下的网络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又与第五编的“民间面向”和第六编的“新媒体的面向”密切相关。从大众文艺观念上的可能性,落实到文学制度的实践,再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这些无疑都可以为当下的“新大众文艺”讨论提供启示。当前围绕“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有许多是以“纯文学”为中心展开的经验描述。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格局中,描述“文学”在“短时段”内的大众化现象,但“大众文艺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百年”的“中时段”问题。文艺与大众的复杂关系,只有在政治、媒介、艺术观念等综合坐标中才能看清楚,它需要宽广的文化视域。《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的创造性就在于,将“当代”的一端,落在了“文化建设”,而不是当代文学界习惯的“文学发展”上。
将视野从“文学”升格到“文化”,足以看清百年的来路。但要看清“当代文化建设”的未来方向,则需要再次“升格”,从“文化”提升至“文明”。按作者的描述,当下所处的是以电子工业、大资本、高科技和视听艺术结合而形成的视听文明时代。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学的未来的焦虑。缓解这些焦虑的办法,不在“文学”“文化”的视野内。《现代的形成与拓路》预言:“在未来文明相当长的时期,视听(声像)虽然占据着文明传播的主导地位,但书写并不能被消除,相反,视听还会依赖书写文字,书写文字会依附和纠缠视听,它会成为它们的灵魂。也正因为此,书写可以在视听的时空里始终保持着相异性的作用,它如幽灵一般把异质性、把远古的记忆持续唤醒。在视听中开辟个人心灵的通道,或许也是共通性的通道。因为,人类可能始终以语言来思维,这一点无法改变,而语言必然以书写文字为最基本的存在形式。”这种关于文学的乐观、执着,来自立足本土、面向未来的中华文明观。作者在该书的导论部分,有专门章节比较中西文化和文明问题。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观念深受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追求绝对性,受其影响的西方文学,可以说是以个人和神学为基础的文化范畴内的文学。中国文学则是一种关于文明的文学,即便有各种个人的叙事,最终总是会卷入大文明的叙事。这种比较论述具有穿透性,相关议题值得深入思考。
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经验极为丰富,所牵涉的理论问题又极其复杂。“当代文化建设”这一论题,亦有热闹的纷扰和迷人的陷阱。这些看起来有无数话可说的论题,恰恰容易让人陷入喧嚣的失语。主编在《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的后记中说,编写该书时力求“体大思精”。这一追求,应该是实现了。“体大”并非仅仅因为该书三册的体量达到了120万字,更重要的还是其处理了百年中国文学几乎所有重要的现象、作家作品和历史议题,其格局、视野的宏大,形成了一种鲜活、有机之“体”。“思精”是洞察之深刻、立论之精当,“体大”与“思精”之间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百年中国文学的敞开,以当代文化建设为起始点,才不会漫无边际,堕入虚空;当代文化建设与百年中国文学,在文明论的视野下才能形成有效对话,不至于自困于眼前的纷扰尘埃。这样的策略,使得《现代的形成与拓路》不仅实现了百年中国文学历史叙事的创新,也开启了百年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06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