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丁晓平,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对于黄公略的名字,学过党史军史的人们都不陌生,毛泽东同志不仅赋诗赞扬,还把“飞将军”的美名送给了他。新中国成立后,黄公略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并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黄公略,历任红五军副军长、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在反“围剿”战役中屡建战功。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领红三军转移路经东固六渡坳,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3岁。9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黄公略追悼大会,并手书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黄公略牺牲后,党组织把他的遗体秘密安葬在江西吉安东固。但他的战友和亲人,都不知道黄公略烈士究竟安葬在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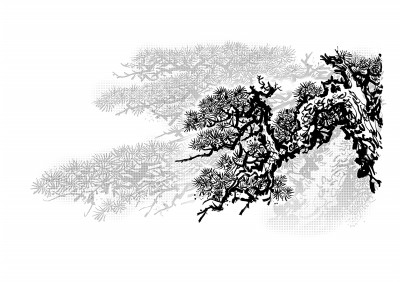
插图:郭红松
上篇:此地长眠“飞将军”
河山从不忘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黄公略的遗骸,始终是党、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的一件大事,也是革命老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心中的一件大事。
1964年,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内务部正式启动寻找黄公略墓址工作。当时带队的是河南省军区许昌军分区司令员高书官。1929年冬,13岁的高书官调到红三军军部,任黄公略的勤务兵。1978年,高书官在接受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访问时说:“中央这次也下了很大决心,认为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找到黄公略同志的遗骨,我们到江西省吉安市东固地区搞了近二十天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坟址还是找到了,遗骨没找到。我分析是红军长征后,苏区人民出于对黄军长的爱戴,怕国民党来毁坟,有意将坟墓转移了。究竟是谁转移的,转移到了什么地方,就无法搞清楚了。因为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山河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遗骨当然是无法找到了。但是,根据我的记忆,还是在原址地域进行了挖掘,终于找到一颗子弹壳,经过分析辨认,一致认为是马牌手枪子弹壳,而当时黄军长用的正是马牌手枪,所以得出了这就是黄军长坟址的结论。后将子弹壳交中央军委了。”
虽然那次寻找未果,然而,对于从未见过父亲的黄岁新来说,她没有死心,也没有灰心。黄公略牺牲时,她还不满周岁。作为黄公略唯一的骨肉,她常以不能寻找到父亲的遗骸为人生憾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采访了父亲当年的战友陈奇涵、李聚奎、杜平、杨世明等多位将军。
1977年11月,陈奇涵告诉黄岁新:“公略同志的遗体,埋葬在东固六渡坳以北的山坡上,当时为了保密,只有警卫连长和军医处医务人员等少数几个人知道真正的墓址,墓址在山坡上,面对齐汾(今齐分村),山坡突出,上有两块大石头,下有两株大松树,我想现在应该可以找到。”1981年9月,杨世明告诉她:“黄公略同志的遗体用一副红油漆棺材葬在该村的西北山上,距村约三里路,坐北朝南。红三军军部副官黄光明同志对我说,以后还要迁到东固去。”而东固本地的老红军邹兴福回忆说:“是葬于一破庵坎下的栗子树下,坑挖有七尺深。”
黄公略到底安葬在什么地方呢?1985年5月,黄岁新带着全家人,专程来到江西吉安。在六渡坳黄公略牺牲地,黄岁新对儿子张忠、女儿张献华说:“外公的遗骸至今还没有找到,我死不瞑目啊!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寻找。”
黄岁新去世后,寻找的接力棒传到了儿子张忠手中。对张忠来说,找到外公黄公略的坟墓,就是了却母亲人生最大的心愿。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忠寻找黄公略墓地的意愿,不仅得到了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东固当地专家的帮助。2020年10月29日、11月19日,召开了东固乡座谈会、青原区寻墓工作推进会,大家不仅找到了新线索,也获得了共识,即:黄公略墓址应是在白云山,坐北朝南,面对兴国县的齐分村,在一座破庵下,边上有两块大石头。
2021年7月8日,张忠向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作了汇报,得到大力支持。同时,张忠还以黄公略亲属名义致信中央军委,希望国家启动寻找黄公略墓址工作。7月14日至15日,吉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专班对6处疑似黄公略墓址进行了挖掘。他们十几次翻遍白云山,对所有疑似地点进行考察。然而,6处疑似墓址都没有找到遗骸,寻墓工作又陷入了僵局,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7月16日,就在张忠准备离开的这天早晨,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工作专班在东固租住的民宿主人刘节明去镇上买早点时,遇见了老朋友李周源。李周源笑着打招呼:“买这么多吃的,来了不少客人吧?”
刘节明回答:“是来寻找黄公略墓地的,黄公略的外孙也来了,找了两天还是没有找到,吃完早饭他们就准备回去了。”
李周源一听,立即来了兴致,神秘地说:“黄公略的墓址,我知道有一个人晓得呢!”
刘节明以为李周源是在跟他开玩笑,说:“谁呀?都找了几十年了,有谁能知道。”
“六渡村的黄富财,他知道黄公略的墓地。”
“是真的吗?”刘节明半信半疑。
“我相信是真的。但是,黄富财的奶奶有交代,只能告诉黄公略的亲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说。”
刘节明大喜过望,说:“黄公略只有一个女儿,他的外孙张忠不就是亲人嘛!”
于是,两人一合计,立即打电话给青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原局长谢拔生。谢拔生立即找到黄富财,向他证实张忠是黄公略的亲外孙。随后,张忠在吉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燕海和谢拔生陪同下,来到六渡村,见到了黄富财。在确认张忠的确是黄公略的外孙后,黄富财带着大家来到黄家的祖坟后龙山上。
一座坐北朝南、面向齐分村的无碑墓穴,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墓边有两块大石头,上面有一座破庵,基本符合老将军们的描述。站在坟墓旁边,黄富财说:“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父亲祭扫祖墓时,会给这座无碑墓挂纸。我很好奇,就问奶奶它为什么没有墓碑。奶奶就告诉我,这是黄公略军长的坟墓,不要对任何人说,只有他的亲人找来了才能说。”
黄富财说的是真的吗?此前报批审核的6个疑似墓址的勘测工作都以失败结束,现在因为黄富财的出现,又要增加一个,超出了工作范围,况且能不能成功,谁也不能保证。
怎么办?现场负责人刘燕海深情地说:“我们不能给历史留下遗憾!”随后,专班果断决定在对这座无碑墓穴公示后,实施挖掘勘测。
8月3日,专班对黄富财指认的无碑墓地进行挖掘,真的发现了人的遗骨。但只有一根小腿骨和两根脚趾骨,棺椁等已全部腐烂成泥。
一切尚无定论,能做的就是等待DNA检测结果了。第二天,专班派专人将遗骸样本送往专业机构进行DNA鉴定。反馈消息很快传来:人体骨骼中DNA含量本就较少,加上遗骨年代久远、降解严重,经多次检测未检出有效DNA数据。
工作又陷入了迷茫,怎么办?经研商,专班一致认为:要尽最大的努力,决不放弃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随后,经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协调,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接手遗骸样本鉴定工作。
在文少卿的记忆里,这次DNA鉴定是最困难的一次。他告诉张忠:“这份样本中,人的DNA含量仅为总DNA含量的约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提取的DNA片段长度只有约80bp(DNA长度计量单位),且存在末端损伤,说明江西的酸性土壤对样本破坏较为严重。”也就是说,这个去世不足百年的遗骨,因为降解破坏,其能够检测到的DNA信息相当于1000年前的遗骨样本。
2023年2月,文少卿团队对黄公略父系亲属进行了生物取样,确认遗骸样本与黄公略父系亲属属于同一晚近父系家族。4月,张忠应邀到复旦大学进行生物取样,确认遗骸样本与张忠为二级亲缘关系。鉴定报告认为:“样本(HGL)应属于黄公略本人。”
5月,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召开专家论证会研究论证,确认送检骨骸为黄公略烈士遗骸。7月26日,正式宣布最后结论:黄公略的遗骸已经找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谁也没有想到,在黄公略烈士牺牲92年之后,一件看似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变成了可能,而且变成了现实。
喜从天降!张忠喜极而泣。为感谢黄富财一家,他特意从北京赶到东固,送去锦旗,上书8个金色大字:“三代守墓,恩重如山。”
下篇:三代守墓英魂在
大爱无声是民心
青山有幸,烈士魂归。然而,当年黄公略到底是如何安葬的呢?黄富财一家三代又是如何坚守传承的呢?
黄公略牺牲后,他的遗体安放在东固背田塅村红三军军医处。因为部队正在转移行进中,首要的工作还是保密,在来不及送往别处的情况下,只能在牺牲地附近安葬。
棺椁哪里来的呢?当年曾参与安葬黄公略的老红军邹兴福在1971年12月12日回忆说:“为了安葬黄公略将军先后买了两次棺材……黄公略将军牺牲后没有立即下葬,而是把棺材先送到指定地点,于晚上安葬。”
那时,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你来我往,打的是游击战,墓地选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从保密工作上来讲,当时红军部队的同志肯定没有东固地方的同志熟悉当地的情况。事实正是如此,黄公略的安葬是秘密进行的,得到了一位名叫胡海的革命先烈鼎力支持。
1901年出生于东固下江口村的胡海,是一名撑船工,20岁时还没有名字,乡亲们都叫他“黑崽”。他在1927年参加东固农民协会,1929年夏任东固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30年2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东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还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黄公略负伤后,胡海奉命赶到现场,配合红军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具体负责安葬工作。黄公略的墓地选在哪里合适呢?胡海想来想去,最终想到了一个人,她就是竹子坝村的东固区原宣传委员黄来从的妻子高春秀。
1928年初,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七纵队和江西独立二、四团经常在竹子坝一带活动。1929年春,红四军营长毛泽覃在竹子坝养伤时,认识了黄来从,并介绍他参加革命。遗憾的是,1930年冬,黄来从遭敌人杀害。黄来从的妻子、六渡村妇女主任高春秀也是地下党员,与胡海的妻子、江口乡妇女主任钟仁桂关系极好。
因为黄公略和黄来从都姓黄,于是,胡海就请求高春秀将黄公略的遗体安葬在黄家的生基(还未安葬的墓穴)里,并要求她保守秘密。高春秀毫不犹豫,郑重答应。9月16日夜,经胡海精心安排,黄公略的遗体被秘密安葬。墓地并非常见的地穴,而是先在山体开洞,然后将棺椁送进洞中。为了保护墓地,没有立碑,只垒了几块石头。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是座坟墓。
1931年11月,以东固为中心的公略县成立后,胡海当选县委委员,毛泽覃任书记。1932年,胡海出任公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胡海被捕,与方志敏一起被关押在南昌,6月15日英勇就义。
一诺千金,沧海桑田。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流转,高春秀始终严守秘密。每年清明、冬至,她都会前来扫墓、祭奠。每当有人问起,她只是淡淡地说,那是黄家的祖坟。
20世纪70年代,高春秀带着儿子黄以清和长孙黄富财给黄公略烈士扫墓。在黄富财好奇的追问中,高春秀才说出藏在她心中40多年的秘密:“这座坟是我们黄氏家族黄公略军长的墓地,他是一位大英雄,是为我们劳苦大众牺牲的!”黄富财不解地问:“奶奶,为什么当时不立个碑?”小小少年哪里知道,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对家乡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围剿,“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
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高春秀,对黄富财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就是你弟弟也不能说,只有黄军长的亲骨肉来找,才能告诉他们!”黄富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敢再多问什么,把奶奶的话记在心上。
1979年,高春秀在弥留之际,把儿子黄以清和长孙黄富财叫到床前,再三叮嘱:“当年,我是受东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委托,要我保护好黄军长的坟墓,还要保守秘密,绝对不能跟别人说。现在,我老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要遵守家训,守护秘密……”
年近花甲的黄富财,老实巴交、不善言谈。但他的每一句话又是那么真诚、朴实和善良。说着说着,他从堂屋八仙桌的抽屉里取出爷爷黄来从的烈士证书和一张张烈士墓志铭的照片。当年,黄家后生踊跃参军革命,黄来从牺牲时才20岁。在东固革命烈士陵园里,还静静地安放着12座黄氏家族烈士的墓碑——黄劳营,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六渡乡司务长,1930年被害;黄香山,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乡苏维埃主席,1931年被害;黄坤元,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团支部书记,北上无音讯;黄书根,1932年参加红军,红三军团四连宣传员,北上无音讯;黄来波,1933年参加红军,红军战士,北上无音讯……
这是一个满门英烈的家族啊!在东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山一水都铭刻着先烈先辈的战斗足迹,一草一木都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第一代守墓人走了,第二代守墓人黄以清牢记母亲的嘱托,保守心中的秘密。2015年,黄以清去世,黄富财开始独自一人承担起守墓的责任。他牢记奶奶的叮咛,保守着藏在心中的秘密,既没有告诉两个弟弟,也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孙子。他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黄公略烈士亲人的到来……
一句承诺,民心可鉴。黄富财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跨越近百年时空,黄富财一家三代信守承诺,接力坚守,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坟茔,更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
2024年9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东固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黄公略烈士的安葬仪式。陵园正中,洁白素净的墓碑上镶嵌着黄公略烈士的铜像。只见他身着红军军服,头戴红军帽,双眉凝聚,目光炯炯,坚定刚毅勇敢地注视着前方。阔别93年后,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在他浴血战斗的地方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团聚了……
这一天,张忠哭了。他站在人群中,默默地说:“妈妈,我找到外公了。”
这一天,黄富财流泪了。他站在人群中,默默地说:“奶奶,我等到了黄公略烈士的亲人了。”
这一天,文少卿应邀出席安葬仪式。他站在人群中,人们看见有两只美丽的蝴蝶围着他翩翩起舞……
黄公略烈士遗骸安葬东固革命烈士陵园整整一年了。英雄,未曾离开,也从未走远……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