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乔天一(文津出版社古籍文献编辑室主任)
地方志和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古籍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0年,李一氓先生在《论古籍与古籍整理》一文中,就提到了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两类古籍,并说:“现在北京出版若干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是个好榜样。”李老文中提到的“北京出版若干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指的就是“北京古籍丛书”。
“北京古籍丛书”是北京出版集团的“传家宝”,至今已有60年的出版史。1958年,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要求北京出版社整理标校北京地方文献,这就是“北京古籍丛书”的缘起。1960年,北京出版社标点出版了《长安客话》,是为北京出版社整理北京地方文献的滥觞。
此后,北京出版社先后组织标点了《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昌平山水记》《天府广记》《琉璃厂小志》《明宫史》《清代北京竹枝词》《宸垣识略》等十余种北京地方文献,于1961—1964年间陆续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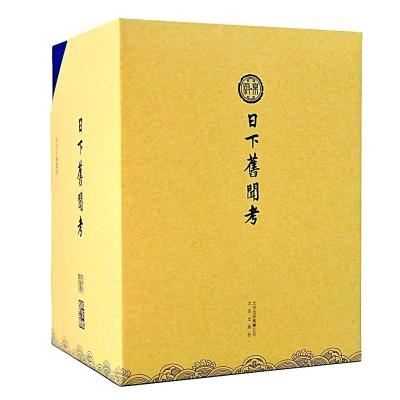
《日下旧闻考》
受到读者反响热烈的鼓舞,北京出版社计划进一步扩大北京地方文献整理出版的范畴,以推动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选题研讨过程中,《日下旧闻考》被纳入出版方的计划。
1964年后,“北京古籍丛书”的出版一度停滞,《日下旧闻考》原已约请瞿宣颖、左笑鸿二位先生标校完毕,只待编校,也被阻断了出版进程。直到1977年,在图书资料室找到标点所用的底本,又约请于杰先生用该书另一版本互校了一次,才重新进入出版流程。1979年2月,北京古籍出版社成立,北京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划归古籍社负责。因此,《日下旧闻考》于1981年出版时,也归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名下了。此后,“北京古籍丛书”就成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招牌书系。
“日下”是古人对京师的别称,清初大学者朱彝尊中康熙己未(1679)博学鸿词科,以布衣授检讨,入直南书房,风光数载,又遭妒被劾去官,闲居穷愁,以著书自娱,借助门生之力,纂辑了一部《日下旧闻》。他摘取历代正史、地方志、笔记、碑刻、诗文等文献中对北京的记载,并访摹断碣残碑、遍征野老遗闻,归纳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等十三门,共成四十二卷。该书搜罗详洽,陈廷敬说它“仰稽天文,俯察地理,及壤土之所生,人物之所宜,推原先王建邦设都之意,布之册书”,是很精到的概括。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不断营建,至乾隆朝中期,京师宫殿苑囿之盛已经远超朱彝尊著书之时,五城、州县界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乾隆帝又是一位以博古尚文自矜的君主,故他批评《日下旧闻》“详于考古,而略于覈实,每有所稽,率难征据,非所以示传信”。在他看来,对朱彝尊的这一著作进行修订,已经势在必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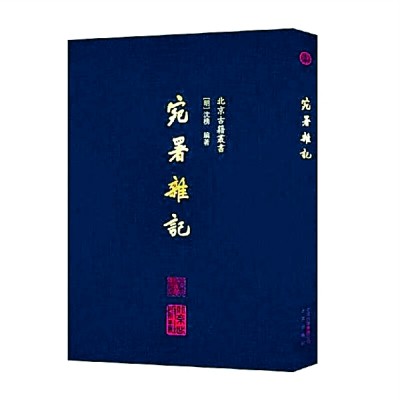
《宛署杂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命大学士于敏中领衔,以窦光鼐、朱筠为总纂官,潘曾起、吴锡麟等为纂修官,对《日下旧闻》做了一番删繁补阙、援古证今的工作,是为《日下旧闻考》。该书除收入康雍乾三朝皇帝关于京城宫囿寺观、名胜古迹的御制诗文以及考证文章外,也增补了大量朱彝尊纂辑《日下旧闻》时所未见的文献记载,还对该书所收文献记载作了一定的考订。
因为做了这样的增补考订工作,所以清代馆臣在纂修《日下旧闻考》时,对书中内容做了很细心的标记。凡属《日下旧闻》所有的内容,在文句开头均标以“原”字;朱彝尊之子朱昆田为本书作过补遗,也尽行收入本书,首标“补”字;凡属馆臣重新增入者,则标“增”字,按语亦加辨别,使阅者一目了然。
这部《日下旧闻考》历时十年而成书,卷帙多达一百六十卷,分星土、世纪、形胜、国朝宫室、宫室、京城总纪、皇城、城市、官署、国朝苑囿、郊坰、京畿、户版、风俗、物产、边障、存疑、杂缀十八门,堪称清代北京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它虽名为对《日下旧闻》的考订之作,实则相当于一部以乾隆朝中晚期为断限的北京地区总志,详细记录了清代北京的城市布局、建筑风貌、社会风俗等信息,并连带叙及京师顺天府管辖各州县的政区沿革、城池官署、名胜古迹等情况,为后世研究京津冀地区的人文地理、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与《长安客话》等书的篇幅相比,一百多万字的《日下旧闻考》可谓皇皇巨著,其整理工作难度也不可等量齐观。为把整理出版工作做好,北京出版社时任领导决定由图书资料室购买一套清代武英殿刊本《日下旧闻考》,作为稿本借给编辑组标点。
当时受整理团队委托,具体负责本书标校的,是著名文史学家、掌故学家瞿宣颖。他是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幼承家学,早年在北洋政府任职,后转而治学,以熟谙文史、博涉多通见长,尤精于方志之学。整理《日下旧闻考》,正是他之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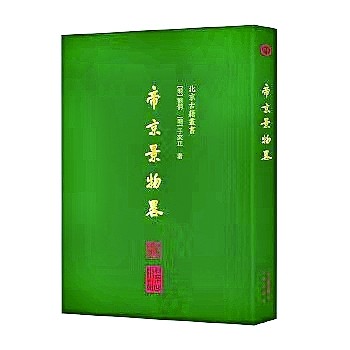
《帝京景物略》
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瞿宣颖已经长居上海,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文献整理工作,也在上海、香港的报纸上写一些文章,笔耕为养。但他不时也到北京探亲访友,与北京文化圈子的联系始终未断。他接受了这份委托之后,在作为整理稿本的清刊本《日下旧闻考》上用红墨水标校一遍,交回出版社。编辑组收到书稿,为求稳妥,又请当时在《北京日报》社工作的老报人左笑鸿在瞿氏工作的基础上,对书稿做了一遍标改,意见也批在稿本上,用的是蓝色墨水。从至今保存在北京出版社的稿本原件来看,两位前辈的工作成果都有杰出之处,称得上互相印证、相得益彰。
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新启动,北京出版社的资深古籍编辑赵洛(1979年2月北京古籍出版社成立后,任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想起这部“大书”,在社内各部门反复询问、寻找,乃至找到图书底稿存档之处,然而各处的回复均称没有见过。难道十几年前出版社同仁以及两位前辈学者为《日下旧闻考》出版付出的心血,就这样化为乌有了吗?
虽然希望已经至为渺茫,但赵洛还是抱着事有万一的心理,找到了图书资料室的韩有生,问他是否见过《日下旧闻考》。令人惊喜的是,韩有生一听赵洛的话,立刻回答说:“有啊!”数刻之后,他托出青布面包裹的八大函《日下旧闻考》,虽然函套表面满是灰尘,但对赵洛来说,这一刻可谓喜从天降:“北京古籍丛书”的出版,不会断线了!
1978年,《日下旧闻考》整理工作终于重新启动。因本书卷帙浩繁,且古籍标校容易出错,赵洛又约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于杰参与本书整理工作,用另一版本的《日下旧闻考》与整理稿本互校,校勘结果用黄色墨水标在稿本上。因此,现在保存在北京出版集团图书资料室的《日下旧闻考》稿本页面上,笔迹是“三色俱陈”的。后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见到这一稿本,赠给它一个“雅号”,叫作“五色斑斓本”。
在经过三位专家跨越十几年的整理标校之后,《日下旧闻考》终于进入出版流程。在书稿审读过程中,作为本书责任编辑的赵洛对校样进行严密把关,不仅校出了排版工作的个别差错,还对整理者的工作有所补正。如《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一《国朝宫室十三·西苑一》里有一句“其巴图鲁侍卫中之奇彻布巴凌阿宁古礼富锡尔璊绰尔图等”,原整理者未作点断,把问题留给了编辑,赵洛与清史学者反复切磋,又经自己细心钻研,终于将这一串人名标点分断开了。1981年10月,《日下旧闻考》终于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实现出版,全套平装八册,定价11元整。在城镇职工平均月收入四五十元的当时,这是一个不菲的数字了。
1982年3月,第二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召开。会上,谭其骧、史念海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专家对新出版的《日下旧闻考》赞誉有加,甚至当场提出,要自掏腰包购买一套。成立未久的北京古籍出版社,由此一举获得了文史学术界和古籍出版界的重视。此后,“北京古籍丛书”就成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招牌书系,而《日下旧闻考》也成了“北京古籍丛书”的代表性著作。
从《日下旧闻考》整理本面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数代古籍编辑薪火相传,对其不断进行完善。1985年,由于《日下旧闻考》出版之后广受各界读者赞誉,且一再有人呼吁重版,北京古籍出版社经过讨论研究,改以精装本形式出版,全套四册,定价“高达”25.50元,依然收获了不错的反响。200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北京古籍丛书”经典品种,四册本《日下旧闻考》仍在其中。
2018年,北京出版社以八册精装本的形式套装出版,使之与久相暌隔的读者再度见面;2022年,北京出版社为展现文献原始面貌起见,又出版了共六函四十八册的宣纸线装影印本。《日下旧闻考》的出版,为一代代的北京文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也使以之为重要代表的“北京古籍丛书”与数代京华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8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