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青春如是·记者视点】
潮涌西部成壮阔
很多时候,扎根西部、奉献西部,已不再只是一部宏大的抒情曲,而更接近于日常,如草野的青、泥土的厚、生活的真。至少在90后、00后这一代青年人眼中是这样的。只在回首往事、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才恍然自悟:“哦对啊,我还真是在奉献西部!”
没有太多仪式感,没有自我感动,也无须烘托与歌颂,他们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做得如同呼吸般自然、饮水般寻常,举重若轻间,将自身命运与西部发展联在一起,与国家蓝图融为一体。他们是自信的一代人!
在南疆戈壁,我们品读到徐灿——一位西部计划志愿者与当地的不了情,他爱着喀拉喀什河的朝阳晚霞,也无惧塔克拉玛干的烈风狂沙;在关中平原,我们嗅闻到张严——一位“高才生兽医”身上的羊圈味,他钻羊圈、钻知识、钻养殖户的需求,于是也钻进了人们的心;在滇西北的高原上,我们目睹了那生——一位“三支一扶”计划优秀代表所要面对的险峻与遥远,那圣洁青春与医术仁心共同盛开在香格里拉。
他们脸上笑容灿烂纯真,自称享受着“远方与眼前合二为一的快乐”。他们热情又谦逊,不认为自己比当地人更先进,是“施予者”“提供帮助者”,而认为自己是一个“接受馈赠者”,一个与西部地区平等相处、守望相助的朋友。这群青年如是看待西部、走进西部、扎根西部,更具有时代意味!
的确,经历了改革开放、西部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大潮洗礼,西部已今非昔比。西部很多地方相对落后的刻板印象,被一批批青年人接力打破、消磨。他们掘其魅力、赋之活力,让西部一个个小镇村庄、一片片田野山林,有了更多供人们施展才华、挥洒青春的空间,让一个充满朝气的西部呈现于世人眼前。
也由此,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有了更为丰厚的载体,让我们记者采不尽、记不完、看不够。我们权且攫取了三位青年人西部时光中的几个片段,透过这几朵浪花,观探由无数个青年人汇聚起来的、奔腾在西部的、平凡又壮美的人生河流。
(《青年说》观察员 彭景晖)
与大漠戈壁相拥的诗行
光明日报记者 李丹阳
二月的风,裹挟着塔克拉玛干的沙粒掠过皮山县时,徐灿正站在一片覆着薄冰的葡萄架下。远处,昆仑山隐在灰白的雾气中,雪线低垂,仿佛天地间悬着一幅未干的水墨。
三年前,这位安徽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成为西部计划志愿者,他背着行囊踏上新疆这片热土时,那时或许未承想到,他的人生会与南疆的晚霞、维吾尔语的音符、沙漠边缘新生的树苗,以及一位名叫古丽苏姆的姑娘,深深纠缠成一首悠长的诗。
初到皮山,徐灿便参与了隔离点的防疫工作,屋里的白炽灯是徐灿对新疆最初的记忆。直到某一天,他照顾的一位维吾尔族老爷爷艾合麦提回家前,突然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纸,用维吾尔语写着“谢谢你,欢迎来我家做客”,背面还附了家庭住址。笔迹细长,在他眼中像喀拉喀什河黄昏时分的粼粼波光。那一刻,徐灿忽然明白:这片土地从不吝啬以最质朴的方式拥抱远道而来的人。
时光荏苒,这片土地展现出更多迷人的地方。还记得一个夏天午后,徐灿和一行人去乡镇调研,正赶上巴扎日。在欢快的麦西来甫那旋律中,他闻到弥漫在空气中孜然烤肉的香气,看到女孩子们穿着色彩斑斓的艾德莱斯花裙,多才多艺的维吾尔族大叔们演奏着许多他不认识的乐器,人们三三两两聚在葡萄架底下载歌载舞,旁边的桌子上摆着香喷喷的烤包子、刚出炉的馕坑烤肉、通透如玛瑙的葡萄……他驻足于葡萄架下,看阳光透过叶片在小路上投下的细碎金斑,恍惚间竟分不清是南疆的日光太炽烈,还是人心太滚烫。
在和田地区团委的支持下,徐灿主动承担起对当地青年村干部、青年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工作。在第三届新疆南疆五地州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举办前,为了联系种子选手,他在乡、村到处寻找有潜质的青年,就连去吃饭、买东西的时候,遇到国通语不错、符合要求的青年,都会邀请其参加。很长一段时间,超市的老板一看到他,就会打趣:“又跑到我家超市找选手来了?”
也是那时,他遇到了现在的未婚妻古丽苏姆。“遇见的那天,她身边围着一群村里的学子,她正用流利的国通语向他们宣讲大学助学政策。得知她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我当即邀请她担任我们参赛队伍的指导老师,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徐灿回忆着,那段日子仿佛一段青春的诗——他们一起熬夜给选手改稿子,一起聊着新疆会越来越美好的话题,他们的队伍不负众望成为大赛冠军。她教他用维吾尔语写下“伊尔凡江”(意为智慧),他回赠她“美盼”二字——取自《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四季轮转,听过了春日的沙尘裹挟着万物复苏的呐喊,看过了冬日的白雪覆盖沙漠如铺开一卷宣纸,徐灿在西部计划期满后选择扎根下来,像胡杨挺立在塔克拉玛干永不停息的风中。
有时他会想起初到新疆时的自问:“我为什么留在这片土地上?”而现在,答案早已写进每一株亲手栽下的树苗、每一场让老乡展颜的直播、每一句当地孩童流利的国通语,还有古丽苏姆望向他的眼眸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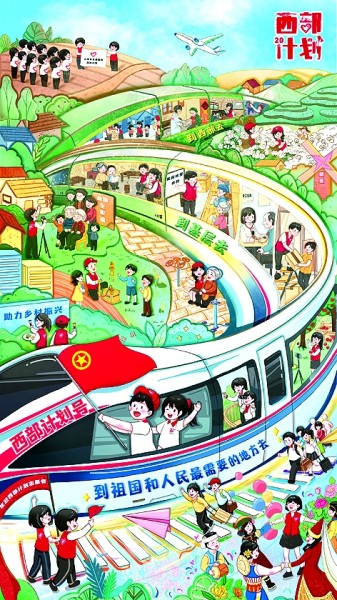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同可爱生灵为伴的欢歌
光明日报记者 安胜蓝
“哎,逮到了!”羊圈中,几番追逐,张严捉住了病羊的两条后腿,“刘哥,抱它头!”
养殖户老刘赶忙上前抱住羊头,乱蹦的山羊立刻乖巧。张严手持注射器,拨开羊背上厚厚的羊毛,一摸便找到血管,精准下针。两秒钟,注射完成。
“羊几天不吃东西,我都急死了,还是你有办法!”刘哥竖起大拇指。站起身拍拍满身的羊毛,张严对老刘细细嘱咐:“这冬天啊,羊圈一定要做好保暖,电暖该开还得开,不然羊容易感冒。打了药以后观察几天,不好的话,再叫我啊!”
张严,一个“半路出家”的兽医,陕西省富平县齐村镇兽医站副站长。在齐村镇,家家户户多少都要养几头奶山羊。山羊养殖过程中难免遇上生病,老乡们都知道,羊出了啥问题,就找小张。
2010年,他从南京农业大学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到山西工作。2021年3月,他看到陕西省“三支一扶”招聘公告。作为陕西人,他立刻报了名,回乡!
这位新上岗的齐村镇基层工作人员热心快肠、爱好钻研,很快便被兽医站的老站长“盯上”了。“小张啊,我快退休了,镇上缺兽医。你看你农大高才生,头脑又灵,不如,你来接?”老站长试探着询问。
“好啊!”老站长的提议正合张严的心意。“当兽医,就能经常下乡,不用老坐在办公室里了!”
真干起兽医,张严才发现,自己还是“想简单了”。“老站长在羊圈转一转,就能判出病情,可我半天也看不出门道。第一次给羊打针,找不到血管,手是抖的。”老乡们也不熟悉这个新来的兽医,还是习惯找老站长。
张严爱钻研,白天跟着老站长下乡钻羊圈学技能,晚上钻书本、钻网站。“就得要多看、多听、多问。”张严说,书本上看、羊圈里学,一个也不能少。“有时症状和书上描述的一样,但实际是另一种病。有时,除了常用的西药治疗外,老乡们还有一些‘土办法’也很管用,都是向他们请教才知道!”张严感慨,“现在,在羊圈一站,哪只羊病了没精神,我也能看得八九不离十了。”
张严渐渐琢磨出了兽医的门道,也品出了兽医的乐趣。在他看来,为动物们治病救命,就是守护自然生灵。“在产羔的季节,我为山羊接生。看着刚出生的羊羔,总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丽。”这种感受,是他在城市工作时不曾遇到却一直向往的。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乡亲们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放下电动车就钻羊圈的“怪后生”。有的老乡直到今天也想不通,这么一个在大城市读书的秀才,为什么跑到他们这里钻羊圈。但他们也死信,这是个眼头亮、有念想的好后生,钻羊圈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无论奶价波动、生意转型还是娃娃择业,乡亲们总爱向他讨个法子。
每当从羊圈出来,张严总习惯性地闻闻衣袖。“味儿挺大!”他笑言,“人说,有为才有位。要我说,干兽医,有味才有位!”然后收拾好医药箱,骑上电动车,顺着乡间小路,驶向下一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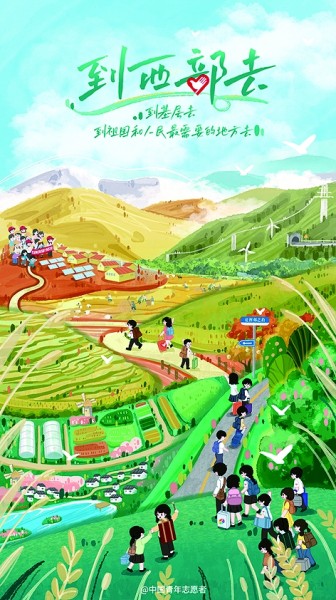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向高山峡谷挺进的脚步
光明日报记者 殷泽昊
如果说翻山越岭时,人要对着大山喊上一嗓子,用回声来给自己壮壮胆、鼓鼓劲,那么藏族女青年那生往往喊了也听不到。她翻的山太高太大了,当地人描述为“人在天上走,鹰在脚下飞”。行走在茫茫天地间,穿行在存在了千万年的高山峡谷,在动的仿佛只有她自己一人。
4年前,那生初来滇、川、藏三地交会的羊拉乡,半路驻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偏远,尽管自己成长和求学的地方也不算繁华。这位青海大学医学院藏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参加云南省2021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募时,知道要去的地方比较艰苦,但她还是坚持要去。
“学的是藏医,服务的是藏族村民,太对口了!”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卫生院,成为她梦想照进现实的地方。
她到来后,那位居住在深山,常年要走4小时山路去卫生院的老奶奶取追,在家就得到了医疗服务,再也不用忍着病痛跋山涉水。“打针不疼,动作麻利,针灸推拿舒服极了!”老奶奶第一次见到那生,便喜爱地一直盯着她看,“这个门巴(藏语,意为医生),像孙女!”
和同龄人一样,那生不喜欢煽情,她认为在西部的乡镇做救死扶伤的事,已经很酷。乡卫生院人手太紧缺了,科室不全,这逼着那生成为全能的“六边形战士”。
乡里中老年人很多,许多人患有关节炎、风湿、肌肉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可用药浴!”2022年起,那生反复申请建议,用药浴来改善血液循环、疏经通络,缓解经络瘀阻引起的疼痛等不适症状,辅助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治疗。建议得到了院领导支持,羊拉乡卫生院于2023年6月正式开展了药浴治疗。
“不用再去远远的州里了,家门口就能药浴了!”村村寨寨奔走相告,病患者都赶来了。要是看不见那生,大家都会问:“那位年轻的门巴呢?”
年轻的门巴,恐怕又在翻山越岭、下乡医疗去了。每逢雨季,羊拉乡道路坍塌是常事,医疗物资要靠人背马驮,“很多时候马也走不了”。身材瘦削的那生和同事们背上生活用品和药物,徒步走进深山里,为村民进行免费治疗。
就在2023年的雨季,那生和同事遭遇严重塌方,又离村寨很远。山路崎岖,要一道梁一道梁地翻;医疗器械金贵,一点都不能磕碰。从天亮等到天黑,村口两旁夹道迎接的村民,终于远远望见了医疗队。
在接受采访时,那生已经记不清那次跋涉累成了什么样子,反倒笑着说:“不算啥子嘛,我滑倒的次数最少!”正是在那个村子,她听说了村民这样的说法:冬天的山坡上,那条白白的一道,可能是雪;但在夏天,那条白白的一道,肯定是门巴的队伍来了!
“于是我真的体会到,原来我与这里的老乡,对彼此是这么重要!”那生说。
在那一派灰黄的高山上,在那一派碧翠的峡谷中,那生的身影,的确洁白如雪。
(本期选题支持:邱玥)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1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