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吴新苗(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北京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戏曲重“抒情”而不擅长叙事,人物塑造“类型化”,远不及西方戏剧刻画“圆形人物”的功力。但事实上,一些创作一味盲目套用西方戏剧的编剧法则和技巧,刻意追求复杂叙事,导致人物形象分裂模糊,甚至创作出的剧本与戏曲表演艺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呈现的故事和人物也不符合中国大众的审美诉求。其实,中国戏曲有着完备的编剧理论与方法。
具有完整的剧作法体系与独特审美内核
中国戏曲很早就建立起了完整的古典剧作法体系。明末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剧作家李渔曾说:“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他自信把握住了戏曲这种文体的“法脉准绳”,并在《闲情偶寄》中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从李渔对戏曲创作“法脉准绳”的系统总结,到众多戏曲理论家、剧作家的不断探索,再到金元至明清时期成千上万戏曲作品中蕴含的创作理念、方法和技巧,它们共同构建起中国戏曲剧作法体系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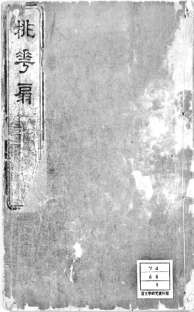
《桃花扇》剧本。资料照片
在这个体系里,起点是剧作家为什么要写一部戏曲作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娱神、娱人、娱己,这对应着传统戏曲演出的三种基本模式,神庙剧场演出、厅堂堂会演出和商业剧场演出。三种创作观念中,“娱”是共同的因素,体现了戏曲艺术最根本的文化功能。为了将这种娱乐功能放大到极致,中国戏曲形成了融合音乐、舞蹈、诗歌、美术、杂技等各种表演形式的综合艺术。通过诉诸视听技艺,以美观动听的娱乐方式,传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肯定,对人性人情的歌颂,也包括对腐朽丑恶现象的批判和揭露。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戏曲艺术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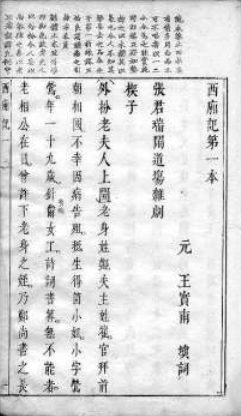
《西厢记》剧本。资料照片
中国戏曲编剧在语言、叙事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独具匠心。从历史发展看,戏曲的语言运用规范成熟较早,这是因为在戏曲出现之前,《诗经》、乐府、唐诗、宋词为其提供了深厚的诗歌传统,戏曲的主要构件——“曲”,自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历代戏曲家对曲词科白写作的讨论,既有对诗词技法的借鉴,也基于日益自觉的戏曲文体意识,比如注重追求“本色”“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清代钮少雅的《九宫正始》与王奕清等人的《钦定曲谱》,直至近代吴梅的《南北词简谱》等韵书、曲谱著作,皆是对南北曲音韵、格律的系统规范,指导戏曲创作者如何写出符合演唱要求的曲词。
关于戏曲编剧叙事的系统总结,则在明代中后期蓬勃发展,金圣叹的评点中已有大量关于叙事方法和技巧的洞见,李渔的创作理论更从“立主脑”(确立核心意图)、“脱窠臼”(避免陈腐)、“密针线”(结构严谨)、“减头绪”(线索清晰)等方面,为戏曲叙事提供了精辟的指导。戏曲语言即曲词科白的写作与戏曲的叙事并非割裂,恰恰是两者的高度融合与共同要求,形塑了中国戏曲剧本创作完整而独特的美学风范。
语言与叙事,最终都服务于一个中心目标:人物的真实传神。中国戏曲剧本创作特别强调“传神写照”,这与中华民族总体的美学精神一脉相承。李渔提出:“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可谓人物塑造的总纲。剧作家须对所写人物有深切的感受和体验,而具体的塑造功夫,则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语言和叙事艺术之中。
“文律双美”“结构第一”“非奇不传”“曲尽人情”的编剧法则
在戏曲剧作法的体系大厦里,曲词创作上的“文律双美”是基本要求。中国戏曲的曲唱和说白结合,是其有别于西方戏剧最为明显的标志性特征。正如齐如山所言,中国戏曲是“无声不歌”的,不仅唱腔是歌,念白乃至咳嗽、哭笑都带有节奏和韵律。舞台上丝竹管弦伴奏,锣鼓铙钹控制剧情节奏,音乐贯穿始终,曲唱尤其是音乐表现最为集中的部分,这就对曲词的音律有着特殊的要求。曲韵、曲谱正是从音乐角度对曲词写作的规范。然而,曲词的音乐性要求与文人追求的文学性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历史上著名的汤显祖(重文采)与沈璟(重音律)之争,就是对于曲词写作中音乐、文学孰轻孰重的不同看法所导致。在此论争之后,“音律文辞双美”成为戏曲剧本创作的普遍共识。近代地方戏曲虽对唱词格律要求不如古代严格,但仍讲究四声五音,编剧常根据演员嗓音特点选用合适的韵辙。翁偶虹为程砚秋创作的《锁麟囊》中“春秋亭外风雨暴”等唱段,文采斐然又朗朗上口,堪称京剧中“文律双美”的典范。

程砚秋《锁麟囊》剧照。资料图片
在曲词之外,“结构第一”是戏曲剧本创作的重要法则。剧作家有感于生活,提笔之前必对素材进行提炼剪裁,精心构思整体布局、具体排场关目,而后方连缀成篇。戏曲的古典剧作法对其中每个环节都有深入探讨,比如处理材料时“出之贵实,用之贵虚,”强调虚实相生的材料处理艺术;叙事时擅长用双线多线交织描摹众生悲欢离合的境况,尤其是发展出以男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独特创编手法。而在排场关目的设置方面,更是具体而微地体现着戏曲艺术的独特性:人物上下场接续推进,时空转化随心所欲,完全自由;关目与角色布局上讲究前后照应,尤重对称性和中和性,对称美学深入戏曲结构的骨髓,人物设置上生旦、小生小旦可谓一组对称,甚至他们的性格、美丑也形成鲜明的对照;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对称,如《风筝误》“前亲”“后亲”、《浣纱记》“前访”“后访”,皆成对称。这种对称在《桃花扇》中表现更为集中,看其出目标题,从“听稗”对“传歌”、“哄丁”对“侦戏”、“访翠”对“眠香”,直至结局“栖真”对“入道”,全剧都是遵循对称法来进行结构的。“中和”美学也体现在结构之中,我们经常说的古典戏曲冷热场调剂就是如此,即在排场上将群戏和独角戏、武戏和文戏、悲情和喜剧、叙事段落和抒情停顿交替编织起来,张弛有道,形成戏曲叙事特有的节奏,同时也起到调剂观众情感和观剧氛围的作用。
“非奇不传”体现了戏曲编剧叙事上的主要方法。戏曲文本也称为“传奇”,体现出古典戏曲对于戏剧性的追求。古典戏曲理论中有“尚奇”之论,文本中设置悬念、巧合、误会,运用突转、反复来增强传奇性(戏剧性),是最为常见的编剧技巧。这些技巧虽为中外戏剧共有,但在中国戏曲中更具鲜明的民间性和夸张色彩,更符合民间人情物理的想象,如多使用女子易装制造误会,或通过“三迭式”重复情节强化戏剧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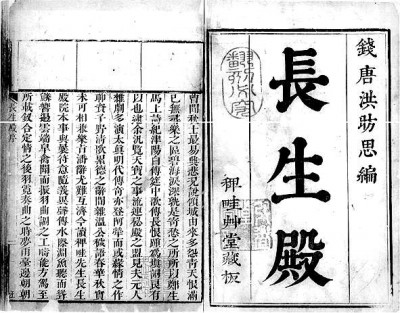
《长生殿》剧本。资料照片
在传奇叙事的基础上,做到“曲尽人情”,是戏曲编剧艺术的最高追求。“曲”,既是戏曲之曲,亦是宛曲之曲。戏曲能够委婉曲折、细腻深邃地展现人情人心,达到汤显祖所描绘的动人效果:“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古典小说中相对薄弱的心理描写,在戏曲中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因为戏曲曲词加上音乐,由演员演唱出来,可以很便捷、细腻地传达人物内心情感,所谓“尽人情”。经典剧目中,主人公上场的一支引子,便能定下其心境与个性基调,如《长生殿》中唐明皇的唱词“端冕中天,垂衣南面,山河一统皇唐。层霄雨露回春,深宫草木齐芳。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既显帝王气象,又透露出其晚年的享乐心态。在塑造人物的关键情节上,往往运用大段曲词,或依事件发展倾诉内心感受,或借移步换景抒发情感,或托身边之物感物起兴,三法交相为用,层层揭示人物内心的丰富层次与幽微波澜,这在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中俯拾皆是。有时,借旁观者之眼来塑造人物,也有神来之笔。如张生看莺莺“宜嗔宜喜春风面”,莺莺看张生“那生忙了一夜”,红娘看张生“乌纱小帽耀人明,白襕净,角带傲黄鞓”,寥寥数语都如颊上三毫,极为传神。
在守正创新中激活戏曲创作的现代生命力
经过千锤百炼的戏曲剧本创作规律与智慧,源于对悠久艺术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持续指导并滋养着艺术实践。它们不仅体现了中国戏曲美学的核心要求,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美学内涵。文律双美、结构第一、非奇不传、曲尽人情,既是戏曲创作传统的重要理论结晶,更是中国独特戏曲美学在剧本创作层面的具体彰显。
进入20世纪,戏曲艺术踏上了探索现代化的征程,这是其回应时代召唤的必然之路。诞生于古代农业社会的戏曲,要在现代社会持续发展,其剧本创作必须符合现代精神与审美。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戏曲工作者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骄人成绩,涌现出《野猪林》《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团圆之后》《沙家浜》《曹操与杨修》等一系列新经典。然而,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偏离戏曲本体审美特质的现象。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坚守住现代戏曲的“戏曲化”,成为新的时代命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的方针。戏曲艺术的本体美学规律及其蕴含的传统创作智慧,是应守之“正”,是“出新”的根基,在当代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当今编剧界正日益重视向传统学习,如近期搬演的昆曲现代戏《瞿秋白》,剧作家巧妙运用传统结构中的对称法则,以“昼”与“夜”交替叙事,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这正是守正创新的成功实践。
当然,传统戏曲剧本创作的经验与技巧中,也存在一些与当代审美不尽相符之处,或仍有待从经典中进一步挖掘提炼。这需要我们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结合当下创作实践有所扬弃。在此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广泛吸收西方戏剧及当代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方能真正做到“守正创新”,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戏曲精品力作。唯有如此,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戏曲艺术,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2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