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杨伟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谈起历史上东西方之间的国际交通线路,“丝绸之路”久负盛名。诚如学界所述,“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在他的五卷本《中国》里,第一次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等地区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主要指西北丝绸之路,又称“绿洲丝绸之路”)。这一名字后来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被广泛地用于指代东西方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它不仅仅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人员往来之路、文化交融之路、宗教传播之路、技术交流之路,在人类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丝绸之路”应包括“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南方丝绸之路”。其中,南方丝绸之路开通时间最早,公元前4世纪以前便已存在。但是,长期以来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相对薄弱。近来,深研巴蜀古代文明、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四川省社科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和该院研究员邹一清的新著《南方丝绸之路史》由巴蜀书社出版,填补了南方丝绸之路通史性著述的空白,亦是当前我国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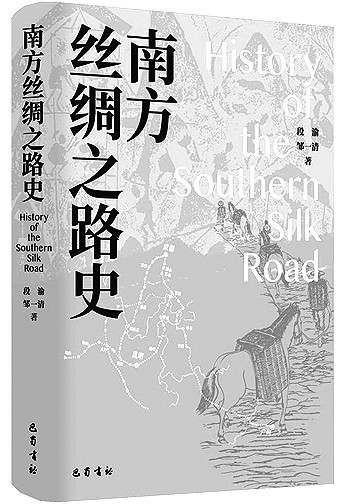
《南方丝绸之路史》
段渝 邹一清 著
巴蜀书社
何为“南方丝绸之路”
对于“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及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各时期指代的主要道路,该著在前言和按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历史时期划分的六章中,进行了概括却不失精细的介绍。作者指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已初步开通”,而“古代四川、云南与南亚、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都是经由这条道路进行的”,“由于这条古老的国际交通线位于中国的南方,所以被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定义,符合历史实际,早已为学术界所接受。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见到了邛竹杖、蜀布,“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之一)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这段话的意思是,张骞在域外见到了蜀布,行经的道路险要,羌人不喜欢,再北一点又是匈奴控制的区域,因此他发现了一条通往蜀地、没有“寇”的良道。这成为汉武帝开拓西南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蜀布”,饶宗颐曾在《蜀布与Cīnapatta——论早期中、缅、印交通》一文中论述,“人只知为蜀贾所卖,故称之为蜀布”。在书中,作者引述印度学者文章论证,成都平原的丝织品进入南亚次大陆,在印度古代文献中有较多记载,如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句。该学者还指出,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早期阶段,印度人不太了解中国织物的材质,分不清“布”和“丝”。
至于中国丝绸在南亚出现的时间,及其与“中国”称谓的关系,伯希和、季羡林等都有过研究。季羡林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推测,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必已输入印度”。伯希和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印度人开始知道有中国,好像是这条道路上得来的消息”。在此基础上,该著进一步进行了讨论,作者在利用最新考古材料对成都平原丝织品出产与行销范围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三星堆文化时期已形成“锦绣之路”的贸易交通现象。
该著还通过文献梳理和考古发现,对存在于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海贝之路”“象牙之路”“茶马贸易”进行了勾勒,丰富了南方丝绸之路物资流通贸易和道路交通范围的研究内容。不仅如此,该著在这些方面的讨论,还彰显了古代文化和文明跨地域交流的特征。以文明互通、互鉴、互融的理念来看待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该书写作的特色和优点。
从古老的“蜀布”“丝绸”等概念在中外典籍中出现开始,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代国际交通线路就已存在。它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辐射,主要经云南,连系今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可达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西亚地区;东南经广西等地可连我国东南沿海,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往北通过金牛、子午、褒斜、傥骆、米仓等“秦蜀古道”入中原,与北方丝绸之路相连。该著对这个交通网络体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格局进行了复原,其中又以向西沟通南亚,向南、东南沟通东南亚和我国岭南、南海地区的通达状况为主,精准指出——“纵观整个南方丝绸之路,在国内形成了横贯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网络”,这便是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
何以“南方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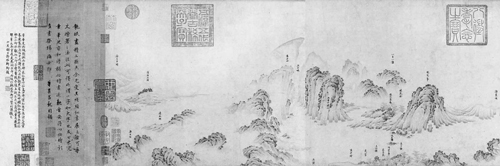
《蜀川胜概图》(局部)【宋】李公麟
该著对先秦至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构成的主要对外交通线路的开通、修复等经营,所依赖的政治形势、经济条件,所促成的沿线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及人群社会、宗教文化等交流局面的叙述,均认识深刻,颇见功力。例如,著作指出,秦汉王朝在巴蜀置郡、移民、发展经济等举措,让巴蜀“从独立王国形态和民族性质的文化,转化为秦汉统一王朝的地域形态和中华民族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华文化亚文化”,也让秦汉王朝得以“利用巴蜀作为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基础,其间尤其加强了对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成都的建设”。
作者对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都会,以及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社会之于南方丝绸之路重要性的考察,不仅改观了以往研究较为重视交通区位“节点”考察,缺少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具象”复原的局面,也有助于理解历代王朝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治理的历史脉络。对四川之外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区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和文化情况,以及南诏、大理于唐五代、两宋时期在南方丝绸之路交通中发挥的作用,该著也有较多阐述。通过作者的细致考察与严谨论述,读者能感受南方丝绸之路上“何类不繁,何生不茂”,交流无远弗届。
该著还重视对制度进行考察。史籍记载表明,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隋唐的近700年间,中原王朝或蜀汉当地政权在沟通和开发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四川西南部、云南设置越巂、益州、永昌等郡,在郡以下设县,对保障南方丝绸之路畅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书中梳理了秦汉、隋唐等时期中国西南乃至安南等地区实行中原行政制度、科举制度的情况,从多维视角展现了南方丝绸之路上制度交流互鉴的影响力。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治理逐渐加强,著作对此背景下驿站设置、官道开通与完善情况做了研究。官道建设和驿站制度的实施,极大提升了南方丝绸之路的通达性,加深了沿线地区各民族的往来,故而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塑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史》一书,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民间交往、人文交流也做了翔实考察。比如,通过青铜器考古资料和文献里的“枸酱”等流布的记述,让“蜀商”群体跃然纸上。隋唐时期,活跃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僧侣,让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了新的气象,本土的中医药文化、茶文化西传,佛教、制糖术等回传印度,无疑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补充。对宋代商人于缅甸地区贸易的贡献,元、明、清时期土官、土司群体在毗邻东南亚、南亚地区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该著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绘。
《南方丝绸之路史》以通史概说为形式,以展示文明交流为主旨,将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南方丝绸之路娓娓道来,实证了它在文明交流史上的地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经由这条道路友好往来、交流互鉴,促进了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交流。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所包含的深厚内涵、所承载的多元文化,已经远远超过“路”的概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薪火相传,丝绸之路成为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也如此。两千多年来时光向前,但这条道路却一直延续不断。如果说历史上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都依其途经地理环境的明显特征而有所指涉,那么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以何可冠?它通过的地理单元更为复杂,高山峡谷似不足指代。两千多年前,张骞称其为“从蜀宜径”,跳出他所处的时局,从文明交流的层面来看,南方丝绸之路或许是一条需要再辟新解的“道路”。《南方丝绸之路史》足以在这方面让读者获得许多新知,做更多思考。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