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赵德发(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
自卑的种子,是在14岁那年的一个春日播下的。
那天,我坐在圈子村联中西边的岭上,身边是一大片正在开花的松树。温暖而强劲的西南风吹来,松树摇摇晃晃,甩出一股股黄烟。我也频频摇动脑袋,想甩掉快要涨破脑壳的烦恼。
真是烦恼呀!我满心欢喜地来读中学,这所刚刚成立的联中却很少上课,多数时间用于学农和学军。目光飞出四里路,我看到了宋家沟东岭上种花生的场面。庄户人都懂一个信号:如果松花开了,花粉飞扬,就该种花生了。于是牵牛下地,耕出垄沟,人在后面播种。点种的多是女劳力和半大劳力,他们挎一个装花生米的小箢子,抓一把就往垄沟里点,点一下放两粒,这活儿我干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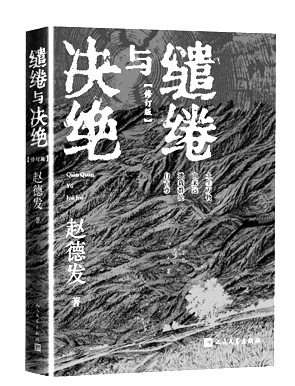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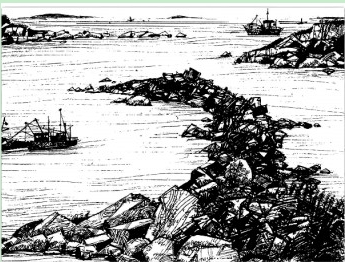
小说《经山海》插图 陈新民绘
身边的松花粉还在纷纷扬扬,我觉得这是在向我发暗号:你不必在这里耗费时间了,应该回自己的生产队里干活。你虽然还是个半大劳力,但干上一天总能挣到几个工分。这时我脑子一热,决定退学。
下午放学回家,我说我不上学了。父母听了都说:不上就不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社员们集合出工的地方,向队长要活儿干。队长想了想说,你跟家科割驴草吧。宋家科比我大两岁,他带着我上山割青草,割满两筐就挑到生产队的驴棚。那里有四头驴,一见我们回来,昂首蹬蹄,十分兴奋。晚上队里记工分,队长宣布给我记六分,我像那些驴一样兴奋。我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年年分不到钱,家里穷得很。有我帮忙挣工分,家境肯定好转。
挟带松花粉的季风刮过,我又有了新的烦恼。那是我割满草筐,坐在山上往西瞅,瞅见圈子村联中的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出出进进,在操场上打打闹闹,我想,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难道我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在生产队里干,从半劳力当上整劳力?然后呢?我看着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庄户汉,想到那就是我未来的样子,心中的烦恼与日俱增。为了排遣烦恼,我揣着从三姨家拿来的歌本上山,自己学会了识谱。又想用乐器把曲子演奏出来,但家里拿不出钱让我买,我就砍一截柳树枝,剥去皮,画上孔,当笛子操练。操练熟了,举到嘴边,指头起起落落,曲子响在心里。多亏这支“实心笛子”,让我的烦恼有所减轻。
我15岁那年初春,被队长派到粉坊干活,兼任会计。我跟三位整劳力一起,每天凌晨起来磨地瓜干做淀粉,白天做粉皮粉条,还推着车子四处叫卖。叫卖时,我羞得满脸通红,声音堵在嗓子里,粉坊头头训我:你个熊样!我鼓足勇气喊,终于喊出声来。把一车粉货卖掉,回来时很有成就感。
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大杂院,里面有牛棚、驴棚、会计室、仓库和茅房。我们的粉坊也在这个院子里。会计室里堆着牛草,是些铡碎的花生秧。晚上大伙聚集到这里开会、记工分,在牛草上或躺或坐。那些时刻,男人们抽着烟说话,驴埋头吃草,牛吃饱了“倒磨”,也就是反刍,院子里“五味杂陈”。渐渐地,我习惯了这些气味,喜欢在这些气味里听人们说话,由此我了解了宋家沟的过去与现在的种种行迹。
这年秋后,宋家沟小学缺老师,大队让我过去。我很惶恐,自己只上了四个月初中,怎能去教学?但是村里缺少文化人,选老师的原则是“识仨教俩”,意思是识三个字的人,可以去教识两个字的。我想,我认识的字毕竟超过三个,就鼓足勇气去了。没想到,学校负责人让我教一个“复式班”,二、四年级同堂上课,有三个学生与我同岁。我念书少,又不会说普通话,他们瞧不起。一些学生不服我管,在课堂上打打闹闹。我深深自卑,每次上课都是高度紧张。
我知道,让他们能瞧得起的办法就是多识字、长学问,一有空就拼命读书。我在村里找,到县图书馆借,几乎每天读到深夜。有一次读《红楼梦》,读完一卷竟然到了早晨。
民办教师的身份还是农民,每到星期天和假期,必须到生产队里干活。推车送粪,播种收割,什么活儿都干。有人叫我“小老师”,但语气里有嘲笑,因为我的力气不如他们大;也有嫉妒,因为我每月能领上级发的四块钱补助。直到我18岁被选为代课教师,到别的村任教,每月交12元买工分,才不到队里干活。
代课教师是临时工,还是农村户口。我与几个公办教师同桌吃饭,别人手里是白面馒头,我手里是从家里带来的地瓜干煎饼,咽下的每一口都带着自卑。
1978年秋天,山东省从民办教师中招收公办教师,我们这里只有三个人考上,我是其中之一。多年的苦读有了结果,按理说应该告别自卑了,但还是不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文化底子薄,距离一个合格教师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填各种表格时,填到“文化程度”一栏就尴尬:写“初中肄业”吧,觉得让人瞧不起;去掉“肄业”二字,心又发虚,觉得欺骗了组织。
第二年秋天,我又在人生旅途上播下一粒自卑的种子。因为心血来潮,我突然想当作家。作家哪能随便当上?尤其是像我这样没上过几年学的人。虽然热情高涨,一篇接一篇,写出就往外投,但都被退稿。有一回,我将一篇小说寄给专发无名作者作品的《无名文学》,也被退了回来。我自卑到极点,在日记里哀叹:“无名尚不许,何望成名哉?”
但我铁了心要当作家,即使25岁时被调到乡里,两年后又去了县委,30岁担任组织部副部长,还是不改初心,坚持业余写作。这期间虽然发表了一些小说,却是一些平庸之作。每当读到同龄人写出的好作品,我往往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志大才疏,惭愧得很。
我明白,我的症结在于文学基础太差,就用三年业余时间读完了电大中文专业,拿到一张专科文凭。1988年春天,得知山东大学招收作家班,我立即决定报考。这年秋天入学后,我看到那些本科生一个个青春勃发,十分后悔自己14岁时辍学,从而在家乡蹉跎这么多年。我想,如果我把中学读完,接着走进大学,我的人生会是另一种样子。
可是,这种想法很快转变了。那天孔范今教授给作家班讲现代文学课。他以几位现代作家为例,讲人生与创作的关系,说人生经验能成就作家,那些坎坷与困顿,反而成为作家跃升的阶梯。我听后如醍醐灌顶,回望家乡,回忆经历,发现了好多好多写作素材。我以在山东大学通过读书所获得的视角打量,认识到那些素材所蕴含的意义,强烈的创作冲动在胸间激荡。
我想到家乡的各种风俗,想到人们在穷困年代里的相濡以沫,又想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折,于是写出短篇小说《通腿儿》。这篇作品在《山东文学》发表,被《小说月报》转载,接着获得第四届百花文学奖。我到天津领奖,与多位名家一起登台,心中郁积了多年的自卑情结终于解除。
这时我觉得,家乡对我来说是一片丰饶的土地,那里的山山水水都藏着故事,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挂着文辞。我一篇接一篇地写,短篇、中篇不断出手。积累到一百多万字时,又想对家乡做更大规模的书写。于是用几年时间准备,而后写出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这部作品聚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写几代人的爱恨情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反响还不错。《缱绻与决绝》问世二十八年后,又被改编成电视剧《生万物》。出演绣绣的女演员提出要到小说作者的家乡体验生活。2023年冬季有段时间,她每天在莒南县相沟镇向当地妇女学做家务、做庄户饭,还下地学做农活,问她收获如何,她说农村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更加理解了绣绣。2024年,这部电视剧在沂蒙影视基地、日照海边和长白山区拍摄完毕,2025年8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
我写完《缱绻与决绝》这部小说时,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长篇小说《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组成“农民三部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还是使用从家乡获取的素材。2018年我写长篇小说《经山海》,主人公吴小蒿是一位女镇长。多亏我当年在家乡机关任职多年,熟悉一些女干部,才将吴小蒿写得活灵活现。这部小说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后,被拍成电视剧《经山历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放。
现在,每当我回老家时,都怀着感恩的心情,感谢故乡养育了我,感谢故乡馈赠我写作素材。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沉溺在自卑之中,而是要激起奋斗的动力,一旦超越了自卑,我就更真切地觉察到故乡的丰饶。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4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