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黄波(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田间的诗歌,曾激起亿万国人保家卫国的斗志和建设新社会的豪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熊辉的《田间诗歌创作研究》无疑是对抗战诗歌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明确指认,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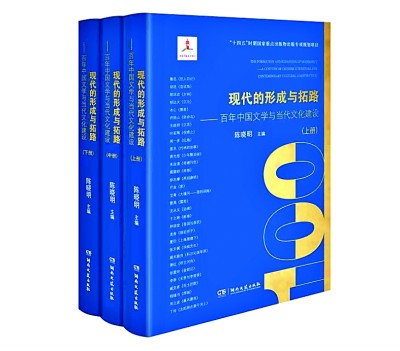
《田间诗歌创作研究》熊辉著 人民出版社
田间本名童天鉴,1916年出生在安徽农村,先后求学于芜湖、无锡和上海等地。后辗转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解放区工作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任职,之后一直在河北省从事文艺创作和领导工作,直到1985年病逝。田间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出版处女作《未明集》,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的苦难生活,也预示着田间开始踏上社会革命和民族独立的征程。在战争中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战斗诗人”和“大众化诗人”,曾被胡风称为“战斗的小伙伴”,被闻一多喻为“时代的鼓手”。此间,田间先后出版了《中国牧歌》《给战斗者》《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和《亲爱的土地》等诗集,这些作品聚焦民族的独立和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田间迎着时代新风创作了一批歌颂和平、歌颂新社会和工农业建设的诗篇,比如《我的短诗选》《天安门赞歌》《汽笛》和《赶车传》等诗集便是其中的代表。之后,田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前往福建前线慰问战士,创作了组诗《志愿军凯旋歌》、诗集《英雄歌》和叙事长诗《英雄战歌》等。田间也曾到内蒙古、云南、新疆等边疆地区考察,继续保持着对时代的热情歌唱,先后创作了《马头琴歌集》《芒市见闻》《长诗三首》和《天山诗草》。田间一生创作颇丰,先后出版了30多部诗集,是中国新诗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且出版诗集最多的诗人之一。对于田间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探索、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现实主义”诗人,专著《田间诗歌创作研究》对其抗战诗歌和革命诗歌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进一步了解田间等一大批从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走来的诗人,有助于我们认识敌后抗日运动的历史价值。从革命圣地延安成长起来的诗人贺敬之在给《田间诗文集》作序时认为,“革命性”和“人民性”是我们认识田间的基本出发点,我们要杜绝采用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标准去衡量田间的诗歌,否则我们自身便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中。专门从事田间研究的专家郭怀仁同样认为,评价田间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些言论无疑都指向了田间诗歌的社会历史价值,是对田间诗歌之于中国社会革命、中国抗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之意义的肯定。为此,《田间诗歌创作研究》从艺术和思想两个向度出发,在复杂的时代语境和中外文学关系视野下,挖掘田间作品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呈现出与时俱进且有深厚民族情感的诗人形象。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难道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才能发现田间诗歌的价值?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田间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乃中国抗战诗歌历史上的经典之作,该诗创作于1938年,时值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生”与“死”、“荣耀”与“卑贱”之间映衬出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人们记住了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因为这些作品曾激起了国人的抗日勇气,也记住了《赶车传》和《戎冠秀》这样的长诗,因为这些作品彰显了社会革命理想。然而,我们却忽视了田间诗歌艺术的探索之路。实际上,田间诗歌对情绪的书写易于产生跌宕起伏的内在节奏,即人们所说的“鼓点”,进而创作出短小的诗行。这是田间对诗歌形式的理解和发现,也是他对郭沫若以来诗歌内在节奏传统的承继。他在新诗如何表现大众且如何被大众接受的“大众化”探索中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积极提倡并创作“街头诗”,缔造了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文艺的醒目风景。
《田间诗歌创作研究》阐明田间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力的诗人。长期以来,田间被置于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对其作品的国际视野和海外传播缺乏周全梳理。田间在现代化程度极高的上海生活多年,对租界洋人及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使其产生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他求学于英语文化氛围浓厚的光华大学,对外国诗歌和文化的了解非常深刻;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抗美援朝的采写,为建立国际友好外交关系而努力奔走,均体现出他并不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政治抒情诗人。与此同时,田间的诗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了英语诗坛,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被翻译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力的诗人,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拒绝阅读和研究他呢?
《田间诗歌创作研究》的出版是新时代的需要。对田间诗歌创作的研究不单单涉及诗歌的接受和审美问题,而是关乎民族精神遗产的大事。像田间这些为人民大众和民族生存而奔走努力的诗人,其作品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理应闪耀诗史,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赓续的文化遗产。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1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