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文学与故乡关系辨析】
作者:王瑜(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故乡作为地标走进文学殿堂与文学创作走不出故乡内理相通。凡文学创作总少不了“故乡”的支撑,灵感涌现、故事原型、文脉传承渗透着作家的成长经验,情感羁绊、写作意义等蕴藏着创作者的故土情结。同样,故乡作为文化母题成为人类心灵港湾与精神家园的象征,离不开文学作品的助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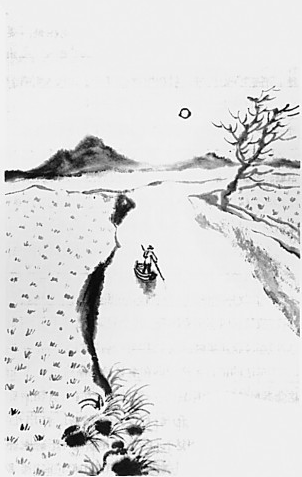
汪曾祺《故乡水》 老树画画绘
用文字镌刻乡愁
土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作家创造出的文学世界大都与其出生地关联紧密。美国作家福克纳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可以说,故乡在作家创作中首先是以土地为承载体的物理空间,包括山川、河流、平原、祖屋、集镇、城市等。沈从文笔下的溪水、青山、渡船、吊脚楼,以及端午节赛龙舟、下河抓鸭子的民俗活动组合出优美质朴的文学化湘西,在展现故乡地理景观的同时勾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端木蕻良说过:“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这种把生命融入土地的信念,在萧军、萧红笔下是对东北大地的守望与凝视。他们以土地为画布展现国仇家恨,写出了人民大众与侵略者的抗争。不同作家关注的视野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不论是颂扬、反思还是批判,其文学世界的建构大都源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回归故乡往往意味着创造力的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关仁山《麦河》、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每个作家都几乎花费大量的笔墨探寻人和土地的关联,落点几无例外地指向故乡。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生辗转奔波,居留故里的时间很短,但作品里念念不忘的都是故乡。故土的河流、沙洲、街镇、房屋、田地、学校,高邮土地上的物产美食都是他的心心念念,《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豆腐》《端午的鸭蛋》《干丝》《四方食事》《家常酒菜》等作品都是他故乡情结的见证。《萝卜》中他写道:“萝卜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或者不如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感受过各地不同种类萝卜的各种做法后,汪曾祺对家乡萝卜的赞美超越对食材本身的关注,写的是舌尖上的乡愁。
远离故乡,远离童年,成长中的经验把我们与过往关联起来,形成一生的美好回忆,组建起高度个人化的记忆库。在这个意义上,食物与炊烟、飞鸟、小桥流水等一起勾勒出故乡,成为文学创作反复描摹的对象。班固写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新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流派,创作者侨寓都市,反反复复书写故乡,是用文字捍卫主体价值,逃离都市文化侵蚀的体现,其本质是以故乡作为精神栖息地,抵抗生活或生命的支离破碎。故乡不是空洞的文字符号,而是支撑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恋乡,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母题,更是人们的精神传承。
文化根脉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原动力
人类走出栖居地的同时拓展心灵宇宙,探索发现生命更大的价值与美好。受地理环境影响,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存形态,造就了多样的文化。作家生于斯,长于斯,不自觉地就将成长中的文化记忆流露于笔端,形成故乡和文学创作的同构。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文学化呈现,更是齐鲁文化原始野性生命力的重塑,他用粗粝的文字展现了历史褶皱中的生存智慧和家乡的文化精神。
故乡是文学的原点,滋润创作者写出优秀的作品。韩少功注目湘西,创作了《爸爸爸》《马桥词典》,展现了湘楚巫文化的神秘性。陈彦的创作长期聚焦于故乡,关注秦腔艺术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在城乡快速变迁发展的时代中,勾勒了三秦大地的文化品格。《装台》中的刀顺子身处困境却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主角》忆秦娥从牧羊女、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再淡出舞台,在秦腔兴衰起落的书写中发掘了三秦大地自强拼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长安第二碗》中,通过秦存根坚守“诚信经营不掺假”的祖训和面对诱惑“祖业不能卖”的怒吼,展现了劳动人民不为利益所诱的硬骨气,凸显了三秦文化的高标。
汪曾祺的笔下没有大人物,也没有空洞的宏大叙事,都是船夫、车匠、乡村医生、伙计、养鸭人等普通劳动者。故乡包容的文化传统投射到他的创作中体现为对人和人性的尊重。汪曾祺以百姓视角写就江南水乡故事,凸显了隐匿的水乡伦理。他的作品不仅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忆,更是对故土文化精神的展现。16岁离开家乡,汪曾祺开启了一生的漂泊,于他而言高邮是精神寄托,也是想象世界中充满温情的心灵栖息地。艺术创作者只有充分感知生活才能深刻认识生活。把个人体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是优秀文艺工作者终身努力的目标。故乡的水孕育出柔而不弱的人性、开放包容的伦理观念和朴素自然的人文理想,共同参与建构了汪曾祺灵动淡远的文学世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写作比拟为“蚌病成珠”,强调创作是个体丰富经验的展现。故乡就是最初进入蚌壳的那粒沙,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孕育写作灵感,以精神原动力的形态催生优秀作品。
故乡是文学创作的“起笔”,也是“落笔”
故乡是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是人伦关系的承载,是中国人一生的牵绊,也是他们肉体和灵魂的归宿。汪曾祺说:“一个作者的责任只是把你看到的、想过的一点生活诚实地告诉读者。……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咱们来谈谈生活。”可以说,“谈谈生活”是他创作观的朴素凝结,道出了他写作的重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原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蔡崇达聚焦闽南地区,通过《皮囊》《命运》《草民》构成的“故乡三部曲”将故土的海洋文化、民俗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写了出来。“讨大海”和“讨小海”分别对应着移民精神与日常生计,贯穿其间的是下南洋、返故乡、捡海蛎、织渔网、晒鱼干等绵延数代的集体记忆。在他的笔下,大年三十抱着女儿跳“火裙”、元宵节感受南音社团的义演、看高甲戏表演、西洋乐队和高跷表演交织的葬礼共同构成了故乡人的生活图景。
在汪曾祺看来,一个人是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的。“民族”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文化,“一个中国人,即便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是在文化传统里生活着的”。他同样重视民俗和节日仪式在创作中的运用,《戴车匠》《端午的鸭蛋》《我的父亲》《故里杂记》《珠子灯》等为读者展现了江南水乡鲜活的生活画卷。《故乡的元宵》中,汪曾祺写了玻璃方灯、白明角琉璃寿字灯、红琉璃泡子灯、珠子灯、兔子灯、绣球灯、走马灯,以及人们赏灯的民俗活动,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高邮的灯节盛景。
仪式尤其是节庆仪式是一个特定群体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能够让人们在共同的信仰中体会生命的律动,以情感为纽带感受“共同体”的温暖,强化个人的社会归属。荣格认为除了个体即刻的显性认识,艺术创作还有更深远广大的精神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和非个人性本质,“不是思辨性的,也不是哲学性的,而是经验性的”。辨析故乡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集体性、经验性的考量或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认知。节日是集体共同的文化记忆,节庆活动更是人们的集体狂欢。文学作品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集体观念与文化归属。故乡是人们集体认同和心灵世界建设的基石,也是个体文化认同的落脚点。
高适有诗曰:“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远离故土,在他乡发挥价值是现代人生活的常态。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是记忆的重现与重组,虽然要运用特殊的写作方法,但主要是作者体验和内在经验的外化。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基础,表达思想感情,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特定群体共享的审美经验。故乡是文学创作的“起笔”,也是“落笔”。关中、燕赵、塞外等黄河流域地理辽阔,山川壮美,民风粗犷豪迈,孕育出雄浑刚健、悲壮慷慨的审美趣味,形成边塞诗、豪放派的文学创作风格。江南、巴蜀、湖湘等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湖泊广泛分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饶,文化积淀深厚,民风细腻含蓄,滋生了精致、柔美、感伤、委婉、内敛的审美追求,造就中国文学中的婉约取向。审美经验的聚合推动“共同体”的产生,催生集体意识与个体心态,进而影响集体、个人的生活模式与行为方式,参与建构出中国人世世代代延绵不息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9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