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李振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朱宇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常务理事)
烛光流转,楼台寂寞。卓越的古典园林与建筑家、书画与散文名家陈从周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先生早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学系,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杯酒劝长庚”的豪兴,也披染着浙中山水寺园的千载余情。后来他拜入“大风堂”,成为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一时画名鹊起。又以独具一格的方式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锋芒初露,得到老一辈建筑家陈植先生等诸多前辈的慧眼识荐。1952年后,他领衔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中国建筑史和园林史研究,就此将一身的诗词气韵、书画骨力和山水精神,贡献于中国建筑园林之美的探索。

在同济执教的风雨数十年间,先生独辟蹊径、心摹手追,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到古典建筑、从诗书曲画到山水园林、从国学研究到“八十年代”学风的跨越和融汇。仿佛“竹里馆”中的王维、庐山草堂间的白居易披云破空而来,为我们留下了如诗的文字、如画的园亭和如缕的学术思想。
先生教诲我们,中国传统建筑之美,美在整体格局和人文环境,美在既有规制与权变机动,美在格物致知与古今传承,美在能工巧匠与土木形态……他特别提出了“物情、物理、物态”这样的概念,来表达对这一独特美学体系的认识。
物情悠然
先生最爱辛稼轩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浙江官话抑扬念出,配上他高鼻细目的神情,如横岭逶迤,水波回荡,令人情思悠然。
如果说前辈建筑巨擘梁思成、刘敦桢二公致力于寻求古典建筑之美的一般规律,陈先生则似更关注建筑与城市、人物在历史长时段中共同生长,休戚与共的情态脉络,或是时代律动中的参差多态,与今日“公民建筑”“体触感”等学术视角颇为贴近。
这份“悠然”的物情、人情,或许来自无可复制的时代背景与交游圈的浸染。人说陈先生画从张大千,曲从俞振飞,红学亲俞平伯、冯其庸,散文则亲叶圣陶;其戛戛独造的园林之学,则紧紧追随着李格非、文震亨、计成、李渔、沈复、戈裕良等人的步履;在中国古典建筑研究领域,更尊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为师。他在“园宅篇”之《拙政园的演变与掌故》一文中,引用清初大画家恽南田《瓯香馆集》中描述当时园景的文字:“自南轩过艳雪亭,渡虹桥而北,傍横冈,循磵道,山麓尽处,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为湛华楼,与隔水回廊相望,此一园最胜地也”。先生边引边叹:“惜士能师往矣,未能及见此文,不然必拍案叫绝,频频作笑也”——他对刘敦桢先生的殷殷之情,让人想起北宋苏东坡对恩师欧阳修的时时惦念:“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而“拾余篇”中《朱启钤与营造学社》《姚承祖与营造法原》两文,亦是人情悠悠。后者言及同济大学今存诸多苏式建筑模型的制作者、香山帮名匠顾祥甫先生时,称其“沉默寡言,有所询必诚恳告人,亲自操作。顾公回苏,七十余卒,每遇人道与予相处种种,语多溢美,为之忏惭,今距其下世近十年矣,每一忆及,令人腹痛”,笔调深挚而传神,让人想起柳宗元的《梓人传》。数十年后,先生主持复建豫园东部时,仍与巧匠们打成一片——大概心头仍会时时掠过“顾公”的仆仆身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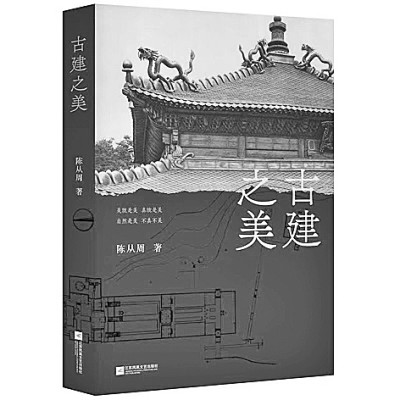
《古建之美》 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由人情及于物情,则可见于“园宅篇”之《恭王府的建筑》一文中,悠然的布局描述:“花园的正中,是最饶山水之趣的地方,其东有一院,以短垣作围,翠竹丛生,而廊空室静,帘隐几净,多雅淡之趣。院北为戏厅,最后亘于北墙下,以山作屏者即福厅。西部有榆关、翠云岭、湖心亭诸胜。府墙外东部尚有一王府,亦宏大,醇王府所在。这些华堂丽屋,古树池石,都给我们调查者勾起了红楼旧梦”——这样逻辑清晰、场景饱满,而又暗含深致和理趣的布局描述,实在是寻常论文所难以企及的。
“园宅篇”之《西泠印社内的营建布置》一文末尾的数行隽语,颇能概括这一悠然之情与峥嵘之气并重的艺术格调。行文亦是以凝练惊艳的四字句,错杂于悠长舒缓的散句之间,予读者以特殊的阅读快感:“至于以泉衬石,水随岩转,不意如此低小之孤山,竟有此许多甘泉,而经营者复能利用之,方见其学养之功也。印社先辈,皆精书画文章,宜其有此佳构为湖山生色也。”
一腔深情,仿佛与硖石诗魂、孤山泉脉、印社先贤共奔涌。
物理俨然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是《短歌行》中的四句。先生带领师生测绘古建筑时,则将其改作朗朗上口的四句诀:“眼明心细,找到南北,绕屋三匝,有轴可依”。这是运用当代建筑学方法进行实地测绘的原则:以敬畏之心仔细观察,依据地形环境确立方位,寻求建筑与相邻建筑、街道、河流的整体关系,画出看不见的曲直“轴线”,仿佛“物理俨然”。
先生曾经问我们,为什么说“牡丹富贵花中王”?我们答不上来。先生解释道,牡丹是一干三枝,一枝三叶,如三公九卿,遵从礼制,暗合着古代的职官制度。而建筑也是表达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譬如东西三路、南北三进……
先生尤长于文史资料的钩稽解读,认为研究古建之美,必先从历史制度与风俗人物入手,纵横论之:查相关方志,读历代笔记,考碑刻铭文,访掌故传说。江左岭南,华北陇西,都在先生的眼里和心里。这一近于“人类学”的视角,当然是与先生丰厚的学养分不开的——相关古建筑的地望形胜、沿革流变、兴衰历程、人物掌故,往往仅以数百字,就讲得历历如画,却又饱含韵致。
如他在“寺殿篇”之《绍兴大禹陵及兰亭》一文中,将禹陵与自然环境的因应关系交代得极尽轻灵简约,余韵不尽:“大禹陵西向,面临禹池,正对亭山,禹池外二小山分列左右,而会稽山环抱其后。”同篇之《江西贵溪的道教建筑》一文中的天师府则“位于镇西端,门临上清宫前街,面沂溪(又名上清溪),对琴瑟岭,北倚西花山,豫樟成林,阴翳蔽日”。而《扬州伊斯兰教建筑》中的普哈丁墓园“位于江苏扬州东关城外运河东岸的土岗上。岗上葱郁的古木与参差的亭阁相掩映,望之蔚然如画。它点缀在运河的沿岸,舟行其下,十分令人注目”。
而如更工细而“俨然”的大木形制与特征,则对照建筑题记与社会背景,作综合的记录与分析、推导。如“寺殿篇”之《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元代大殿》《洞庭东山的古建筑杨湾庙正殿》两文,横向比对江南宋元遗构,缕述建筑各部位的形制演变、年代差异、抽换痕迹,一毫不苟,绝无空疏习气,令人赞叹。
当然,先生亦会关心“俨然”布局、形制中的例外变化,并探求其所传达的社会逻辑与信息。《江西贵溪的道教建筑》描述的天师府后园“虽仅一纳凉台,但其前清水浩渺,樟木葱郁,枕流看山,得借景天然之胜,建筑上亦不必多事增饰,引人有超然世外之感,这与宗教思想有关,构成了另一种园林风格”。
同篇之《广州怀圣寺》一文,更用先生擅长的诗样笔触,描摹了这一与扬州仙鹤寺并称、文明交织的空间成果:“寺之布局极紧凑,而院宇开朗,廊庑回合,极开畅舒展之致。自礼拜殿廊下望拜月楼出花木间,光塔背负,耸现其上,苍天白云,翠盖红墙,宛若仙山楼阁,令人流连难返,庭院静观之妙,于此得之”——让人油然想起清人姚鼐《登泰山记》中“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的句子。或是沈三白《浮生六记》对扬州瘦西湖白塔的描述:“过此有胜概楼,年年观竞渡于此。河面较宽,南北跨一莲花桥,桥门通八面,桥面设五亭……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
这“俨然”寺庭中的“悠然”之趣,仿佛更令人神驰意远。

物态翼然
先生晚年尤喜绘墨竹兰花,一边口诵“虽然高下分浓淡,总是新篁得意时”的句子,一边信笔挥洒,如有神助。那种骨骼劲挺,而又潇洒纷披的翼翼之态,仿佛成为先生区别于其他建筑与园林学者的重要特征。
梓翁才艺之多,世所共知。记得当年先生还曾筹款翻印了古典家具名著《燕几图》《匡几图》,以供学子与同好参考,对红木家具的如玉触感亦津津乐道。此外,先生的教研室一角,还长年倚靠着几根瘦劲树干,那是先生特意挑出的制杖良材,预备亲手加工好了分赠师长与老友。
横抒纵引,不离其宗,亦是先生授课的独到之处。记得多年前一次,陈先生延请昆曲名家来校作讲座,示范讲解表演中的各种情态把握,刹那间满堂溢彩,顾盼神飞——讲座甫毕,端坐前排、担任主持的陈先生徐徐起身回首,畅谈感想,一时切中肯綮,娓娓不绝,台上人伫候许久,终于忍不住,偷偷从陈先生身后向台下的我们轻挥素手,悄然而去——而陈先生犹自妙论不断,不以为意。
种种缤纷爱好,如同大鹏之翼,极大助益了先生的领域贯通与思想升腾。
先生青年时享誉海上画坛的代表作《一丝柳一寸柔情》,是以画面下方气韵悠长柔缓的万千柳丝,铺垫出上端一双团团而栖、墨色浓重的小鸟——这一布局,让人想起北宋王安石描述名刹天童寺的“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的句子。
田园远山间,一塔标出,摄人眼眸,先生却并未止笔,而是由塔及泉,翼翼挥洒:“而路旁泉声益喧,延续数里,清澈见底,荇草蔓生,虽时近中午,溽暑却顿为之一消,古人所谓‘醒泉’者,殆指此类而言了”。此时先生犹觉展翼未足,于是由泉及酒:“晋南的泉,其佳处在醇厚清冽,荇草翠绿若新染,仿佛如饮汾酒,其浓郁芬芳处为他酒所不及者一样。”随后复由泉及田,并稍作摇曳:“这水从霍山山间来,名霍泉,眼底的一片肥沃农田,便是此泉所形成的。如今广胜下寺山门口建了水力发电站,又将泉三七分流,灌溉了赵城、洪洞两县的土地……”
科学发展,学科细化,终会是时代的规律。但这也令中国传统的“泛文人”“泛艺术”社会脱胎换骨——原本诗词、书画、拍曲、造园浑成一体,方能烘托孕育出的建筑与园林审美高致,终究迤逦而远。传统田园社会横向浸润、渗溢的文化艺术脉络,终究不免被日益严整细密的工业社会之纵向专业分野切断。深具东方特征、恢宏融通的艺术共振现象逐渐消失,艺术通才与巨人日益罕见,专业设计者往往缺少必备的创造力与融通力——在这样的语境里,陈先生却以其穿越时代、融通艺林之身,重新接续起被工业时代长期割裂的社会筋脉,重构了中华文人大众与中华传统建筑以及造园艺术的互动互哺,成为面向全社会的建筑与园林审美启蒙者。
初入陈门时,先生已近古稀之年。高鼻长身,漫行鹤立。一件半旧的蓝色中山装,被穿出长衫裹躯般的摇曳味道,仿佛落拓不羁的魏晋名士。可一口风味浓郁的浙江官话,却又如绍兴黄酒,暗透出“江东子弟”的才俊气质,让一众弟子们有阅读鲁迅文章般的亲切。
那时先生正连遭丧妻失子之痛,年华骤老,皱纹满面,如山水皴法般交织出凝重沉郁的神情。而一身汹涌的烟味,却又伴着汩汩的才思而出,剖析古建、指点江山、经营园亭、挥洒辞章,仍是弥漫不散,共人欲醉。
那时我们有幸听先生指点,南下北上,攀跻考察,寄情遣思。岱庙劲柏、登封塔林、侯马古墓、长安碑碣间,留下亦步亦趋的仆仆足迹。而每回经过三门峡、风陵渡的大河弯环,壁立千仞,或是苏州、常州诸府的温山软水、迤逦楼台,总会想到先生解衣盘礴或是对月当歌的豪兴逸情,让我们也情怀激荡、神思飞扬起来——30年过去了,先生那种种超然“跨界”、不拘一格的轨范凤仪,仍令人回味不置。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