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代文体种类之多令人自豪和赞叹。明代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分别各体132类,晚清吴曾祺《文体刍言》所论文体更达213种,其中包蕴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等少数论著外,对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如何深入多元地研究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何建立具有学科意识的文体学研究格局,学者们还缺少探索,颇有坐拥宝山却无从下手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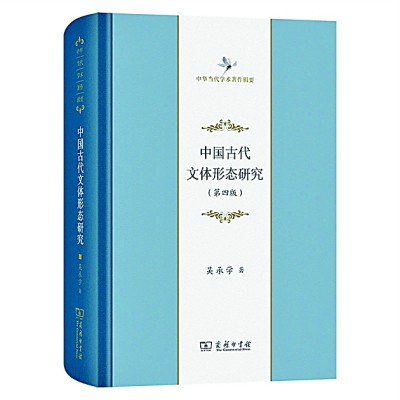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吴承学 著 商务印书馆
从这个意义上看,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吴著)一书的问世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该书初版于2000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既是吴承学的教育部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相关成果,也是他从事文体学研究十余年的经验结晶。当时傅璇琮先生欣然赐序,称赞作者“有一种坚实而敏感的学科建设意识”。所谓“敏感”,是指作者敏锐觉察到文体学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应有而目前尚待填补的重要板块;所谓“坚实”,是指作者不尚空言,论从史出,所得结论有很强的说服力;所谓“学科建设意识”,是指文体学学科既需要理论思考和指导,也需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具体实践,而吴著一开始就展现出这种研究格局,堪称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领航者,又像一盏明灯,照亮文体学研究前行的道路。
吴著初版计十七章,主要选取古代一些虽重要但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的文体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如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诗题与诗序、留别诗与赠别诗、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宋代櫽括词、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酒令(《诗牌谱》)、评点等,另外还讨论“文体学源流”“辨体与破体”“破体之通例”等文体学理论问题。2002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增订本,计十九章,增补了对汉魏六朝挽歌和诗歌文体形态(“诗可以群”)的考察,并将章节顺序调整得更为合理和具有历史时代感,如初版将评点这种特殊文体放置末章,第二版则调整到宋代櫽括词之后,因为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方式,评点到了宋代才真正形成并走向兴盛。在研究中,吴著往往先对文体的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阐发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这种考论结合的研究方式,给当时去路彷徨的文体学研究以极大的启发,引得后学者纷纷效仿跟进。至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文体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成为增长最快的学术生长点之一。
2013年,吴著第三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除改正旧版中一些学理或文字上的讹误,还重拟章节目录,使之更为清晰和便于阅读。另外,增加了“六朝的忏悔文和杂诗体”及“论序题”两章,删减“文体学源流”“辨体与破体”“破例之通例”三章,又将篇幅较短的“留别诗与赠别诗”放入附录,改题为“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因此正文计十七章,属于更加纯粹和名副其实的文体形态学研究。到了2024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第四版,又增加了“秦汉的职官与文体”“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作为批评文体的‘读法’”三章,补入一篇附录“复杂的‘杂文’”,内容愈加饱满厚实,书籍装帧也愈加美观。而吴著第三版删减的三篇文体学理论的文章,则融入了作者另一部集中谈古代文体学理论和古代文体学史的名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这两部书,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成立,都有着柱石之功。特别是前者,先后四版,历经20余年,恰好动态引领和见证了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商务印书馆将之列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无疑是慧眼识珠、采择允当。
正因为既有功底深厚的微观考证,又有全面系统的宏观思考,吴著在研究文体问题时常有闪光的发现,最后的议论也总能高出一层。如将盟誓、酒令、评点、清言等作为文体去研究,本身就具有开创性。但吴著并未止步于对体制源流的梳理,而是揭示出先秦盟誓制度的出现,正反映了礼制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现象;拈出《诗牌谱》不仅是酒令,还蕴含着汉字诗学的丰富意义;指出评点是转向对文本的语言分析和形式的批评,对于文化的普及和古代修辞学、写作学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总结晚明清言的审美特征、时代色彩,以及其在文人心态和思想内容方面的两重性。这就使他的研究上升到了语言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文化学的高度。
吴著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其有情怀、有思想、有活力。他拒绝将文体形态看作形式的空壳,而是将其看作承载着感觉、记忆、情感、心态、审美、制度、文化等诸多内容的综合体,看作人类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实践工具;他对传统文体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满怀温情和敬意,但又不缺乏理性和思考。如他指出“诗可以群”这种注重创作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固有的民族特色,可以有效表达出亲情、友情、同僚之情以及君臣之情。但也指出,诗坛可能因此出现大量歌功颂德、附庸风雅的低劣诗篇,产生大量遵命而作、为文造情甚至重复雷同的无聊作品。“诗歌既可能成为个人性灵的雅品,也可能沦为应酬交际的俗物。”他欣赏晚明清言对功名心和贪欲的蔑视,同时指出崇高的精神和英雄的气度,也易在逍遥闲适的清言世界中消磨掉。“清言所标榜的是高旷,而最终却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头。”他念念不忘回到中国本土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又时时提醒人们要超越中西畛域,打通古今鸿沟,突破学科的樊篱,创造出超越古代文体学的新辉煌。总之,吴著保持了感情和理性的统一,也因而充满张力和活力。在第四版跋中,作者认为“文体研究应该追求一种有灵气、有思想的学术境界”,可谓夫子自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中,作者再次明确地强调,古代文体学研究应将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和现代学术意识结合起来,他还将具体方法总结为“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从而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形成了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呼应,共同推动着具有现代学术高度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使作者不逐潮流,默默扎根文体学研究数十年,最终与其他有志于此的学者一起,积木为林、聚溪成河,使文体学研究辉煌于世,其道大光。如今重温傅璇琮先生序中所说“我们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有一种‘傲世’的气骨”,不由对这样斯文自任的学者肃然起敬!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1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