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孙红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作为晚唐最伟大的诗人,李商隐让历代的译者着迷。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美国诗人宾纳、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华人学者刘若愚到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以及近年来的美国译者罗伯茨、柯夏智等,都陆续出版了李商隐的译集或研究专著。
在主题的层面,葛瑞汉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李商隐的情诗,刘若愚以西方人所熟知的“巴洛克”的概念来界定李商隐的华美、精致与繁复,而李商隐诗中的道德关切则让宇文所安想到了弥尔顿《失乐园》里的善恶之辩。在形式的层面,叶嘉莹把李商隐与卡夫卡比较,柯夏智将李商隐与现代诗人庞德、艾略特相提并论。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比较,恰说明了李商隐是一个“多声部的诗人”,他的文字里有杜甫、韩愈、李贺乃至卡夫卡与艾略特的影子;另外,在西方的语境中,不同论者都试图将李商隐置于某种可认知的框架中,这些比较也为阅读与理解李商隐提供了相对熟悉的参照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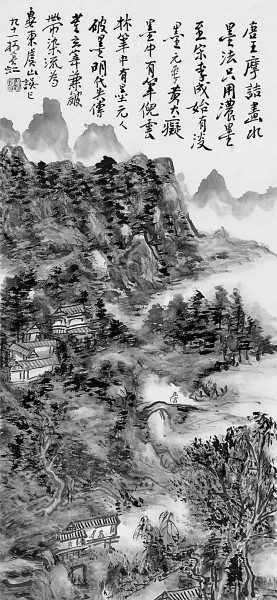
黄宾虹《巴山夜雨图》(局部) 资料图片
翟理斯的简化与省略
翟理斯在其《古今诗选》(1898)中收录、翻译了两首李商隐诗:《夜雨寄北》与《乐游原》。这两首诗写景生动,语浅情深,实际上是李商隐“非典型性”的浅白、畅达之作。在翟理斯的笔下,第一首译诗题为《纪念品》:
你问我何时归来:噢,还不知何时再见,
那晚我们相遇时,雨水将池塘注满!
啊,我们何时才能再次熄灭烛火,
忆起那个雨夜的欢乐时光?
显而易见,译诗丢失了若干细节,寄北、秋雨、巴山、西窗四处最为关键的信息在这里付之阙如。特定的地点、景色与气候消失不见了,弱化了情感表达的附着感。再者,翟理斯对整首诗的理解也是有误的,“西窗剪烛”讲的是设想未来相见时,忆起今日思念故人的情景,在时间轴上先向前然后再折回,线性的时光被转化成连环相扣的结构——由此,现在的想象与未来的回看首尾衔接,构成了一个闭环。而翟译则是追忆某个相见的雨夜,在时间轴上仅仅是向后的回望。
《夜雨寄北》写的是乡思羁愁,全诗缠绵悱恻,这一主题也凸显在诗句回环往复的结构上:首句“归期”与“未有期”形成了一个回环;二句与四句两处“巴山夜雨”又形成了一个回环——由此传递了低回婉转的心绪。这种上下相接、层层推进的构架,赋予了诗歌一唱三叹的节奏感,同时也使诗歌的情思不断深化,形成了荡气回肠的效果。这是内容与形式同构的范例了。李商隐诗写含蓄、摇曳之情,尤喜采用这种回环的形式: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又如“日日春光斗日光”“一寸相思一寸灰”,而“巴山夜雨”的重复又如“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均是表达绵绵不断、纠结缠绕的情感。然而,经翟理斯的翻译,《夜雨寄北》的诗味儿打了折扣,沦为关于往事的慨叹了。
翟理斯的译法得之在俗白浅易,还原了原诗的简洁朴实,但失之在索然无味,关键信息的省略、笼统化的处理导致具体的所指变成了宽泛的一般性描述。他所翻译的《乐游原》也有相似的特点:
夜色将至
黄昏已降,我的心绪不宁
在那古老的山上,我勒住马缰
辉煌的白日
迅速消逝
只留下一片暮色苍茫!
与巴山相似,乐游原同样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地名。它是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多有吟咏,为这一地点赋予了层累的意义:如杜甫《乐游园歌》写道:“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白居易《立秋日登乐游园》写道:“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杜牧《登乐游原》写道:“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乐游原所触发的是凭吊怀古的情绪。翟译中,历史与地理的细节消失不见,同《夜雨寄北》一样,失掉了可辨识的特征。一个地名往往意味着诗的地域性体验,可以勾连起丰富的内容,一旦略去这一指涉,便丢失了诗歌历史与空间的纵深感。
宾纳的内容与葛瑞汉的形式
一首唐诗往往触景生情,有着具体的牵连。在李商隐的诗中,无论是巴山、秋雨、西窗还是乐游原,都是组织诗歌表达与感觉的线索,若将其兴发感动的动因完全取消,那么诗歌也随之黯然无光了。三十年后,宾纳的译本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矫正。他在《群玉山头》的卷首便引用了李商隐《韩碑》中的诗句:“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韩碑》以韩愈为歌咏对象,写的是对韩碑被毁的愤慨,并模仿了韩愈的诗风,表达了李商隐的自我体认。而宾纳卷首的引语也是对这部译集的定位:它也是文化传递的一种方式——文化的源远流长,不依赖于碑刻之类的物质条件,而是无形的、精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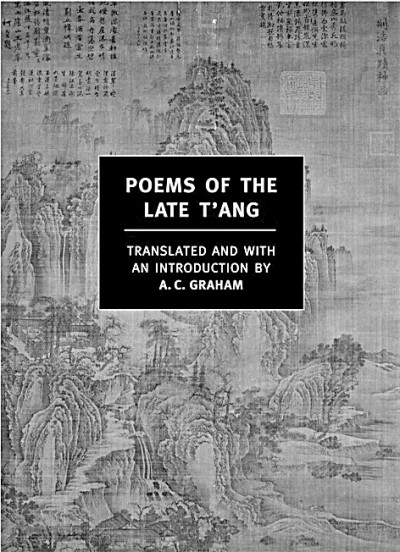
葛瑞汉《晚唐诗选》封面 资料图片
韩愈的文章不因石碑的毁弃而消亡,一首诗的流传也不依赖于原初的形态,即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内容的流传最为核心。这一点体现在宾纳的李诗翻译上。在这部译集的李商隐部分,《夜雨寄北》与《乐游原》作为开篇的两首编排在一起,本身便形成了对翟理斯的一种隐秘的回应。在书后的注解中,宾纳的译集也简略提及了翟理斯的错讹之处。
在宾纳的处理中,乐游原、寄北、秋水、西窗、夜雨等关键信息都得以保存。不过,宾纳专注于内容,所译《夜雨寄北》也是以改写的方式替换了尾句的重复,未能兼顾其循环往复的形式:“噢,我们何时才能再次一起在西边的窗前修剪烛芯?/何时我才能再次听到你的声音,整夜在雨中回响?”
与之相较,葛瑞汉《晚唐诗选》所译《夜雨寄北》则选择了不同的理路,完全复原了尾句的重复,由此摹写了原诗“巴山夜雨”的循环呼应。葛瑞汉尤其注重形式的对应,例如李商隐诗《天涯》写道:“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葛瑞汉还原了其中的顶真修辞,复现了诗中的递进之感,可谓得其妙处。
宇文所安的兼顾和罗伯茨的唯美
单从《夜雨寄北》谈起,宾纳得之在内容,失之在形式;葛瑞汉得之在形式,失之在内容。译李商隐诗,形式与内容的考量自然缺一不可。为此,宇文所安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例如,在谈《燕台四首》时,他指出其中的不可译处:第一首的最后两行“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拆开了“风”“光”二字,与首行的“风光冉冉东西陌”形成呼应,难以传译,而“风光”这个词本身所包含的“风”与“光”的触感与视觉的融合,英文中的“风景”也是难以匹配的。这种讨论反映了宇文所安兼顾内容与形式的意识。这一点仅从其译李商隐《曲江》诗“曲江”一词的译法便可见端倪。
“曲江”如赤壁、乌江或马嵬,也是重要的胜景残迹,唐代诗歌多有提及。如杜甫诗:“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对于曲江,英国汉学家霍克斯采用了“serpentine”(蜿蜒)的译法——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也用了这个词来描述东方的河流,因为构词的缘故,这个词有一种莫名的不祥感;葛瑞汉以“crooked”(弯曲)译“曲”,这个词附带了道德褒贬的外延,有“不诚实”之意;美国翻译家亨顿采用了“meandering”(曲折)的译法,这个词则被过多地用在对河流的描述中,显得空泛、陈旧;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用了“winding”(盘旋、螺旋),又过于稀松平常,缺少一种陌生感。与之相较,宇文所安则选择了“twisting”(扭曲),这个词是跳脱的、突出的,有着一种新奇性,可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去咀嚼其中的意蕴,凸显李商隐的委婉。事实上,这是一种刻意而为的选择。在谈论李商隐诗《筹笔驿》时,宇文所安用“mannered twist”(故意而为的曲折)来反映李商隐的艺术特质,“twist”表达了曲折的意蕴,对应的是委婉。不难想象,宇文所安“曲江”的译法也暗含了这一层考虑。宇文所安尤善于通过一种专注于形式的透镜细察中国古诗,发现其中形式与内容的同构关系。曲江之“曲”恰是曲折、婉转的情绪——这里的“曲”既是空间的、几何意义的,也是诗学的。
当代的译者中,罗伯茨也以同样的选择来翻译了李商隐的“曲江”。如果说宇文所安同时看到了李商隐诗的形式与内容两个维度,那么罗伯茨则注重李商隐的“诗性”表达。
罗伯茨曾全译了李商隐的笔记《义山杂篡》(2014),语言诙谐有趣、平易近人。关于这个译本,美国作家卢卡斯称“李商隐对唐朝日常生活的妙语连珠式的牢骚,读起来就如我们最风趣的朋友发来的短信一般鲜活”。在译李商隐诗时,罗伯茨则主张“保留字面意,专注美学特质”,故意不加注解,从而让李诗跳跃、突兀,具有了先锋、实验的性质。李商隐诗用典极多,译诗注解一般体量巨大,甚至超过诗歌本身的篇幅。罗伯茨却是径直译出,不加任何说明,就连译“青鸟”“蓬山”这类具有文化负载的词,也是直接拿来。在她看来,诗歌一旦意译,就会“让语言变得平滑”,“消除了诗歌意象本来的奇特感”。例如《槿花二首》中的“燕体伤风力,鸡香积露文”,她直译作:“燕子的身形被风摧残。/丁香花上,凝露成纹。”原句以赵飞燕比木槿花的轻盈与不胜风力,以鸡香对偶燕体,译文并不加以解释。《曲江》中的“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她译作:“死时,我将记得仙鹤在华亭鸣啼。/老时,我哀悼皇宫,对着铜驼哭泣。”华亭鹤唳、荆棘铜驼的典故在这里也不加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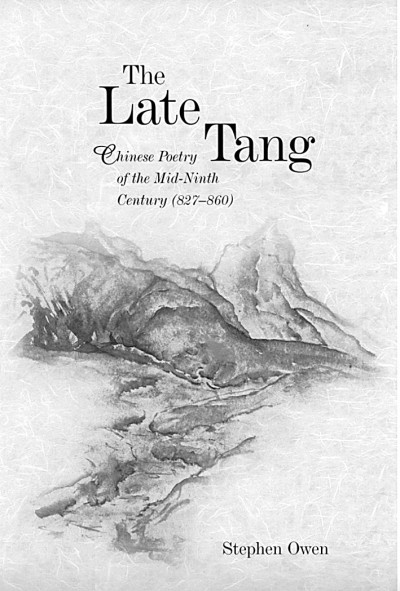
宇文所安《晚唐》封面 资料图片
这种译法造就了罗伯茨所谓的“李商隐专有的古典立体主义:一幅由诗歌意象的碎片组成的拼贴画”。在译文中取消脚注或解释,“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读者接触作品时感受到其中的神秘。”在她看来,“一首诗的价值无须通过阐明或转述意义来体现,而在于意象本身所蕴含的美”。这是一种唯美主义式的策略,留存了诗本身的陌生感,避免让诗歌陷入文字阐释的泥沼中。
赖特的串联与凯利的植入
典故不加处理,置于异质的语境中,无疑制造了突兀而神秘的效果,呈现了一种特殊的诗性。美国诗人查理斯·赖特所推崇的正是这种名词的富集感,譬如描述的堆叠、结构的跳跃、朦胧的想象,以及没有任何承接的句法关系。在一首题为《色晕缺失的风景》的小诗中,他写道:
夕阳已在蓝岭山后落下,
夜幕是一张吸墨纸,
抹去了余晖。
幽暗的庭院。月光透过白松。
无论是夕阳、暮色、庭院、月光与白松等意象的堆叠——不加解释的、纯粹物象的描述,还是四行排列的诗体,对于熟谙唐诗的读者而言,它们所营造的诗意似曾相识。这种熟识感究竟来自哪里?紧随其后的是一首题为《李商隐的艺术家画像》的短诗:
我的画像即将完成
在《白发之书》中。
日落蓝岭,
黄云飘浮。
一分绚烂一分灰烬。
诗中的“我”是含混不清的——它究竟是以李商隐的口吻在自述,还是诗人本人的语气?这是一种故意而为的含混,诗人与李商隐合而为一。诗歌本身便构成了一个文字的画像,定格在日落蓝岭、夜色将至之上,而此时恰恰也呈现了最后的绚烂——它杂糅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与“一寸相思一寸灰”两处诗句,交织了对于时不我予以及对于美好事物绚烂又短暂的叹惋。
赖特所采撷的是李商隐诗中固定化、风格化的元素。最有意思的是,这首诗以美国阿巴拉契亚山的蓝岭山脉对接李商隐诗中的“蓝田”——例如,葛瑞汉的《锦瑟》译诗将“蓝田”译作“蓝山”,从而将当代的关切与李商隐诗歌中的景观无缝衔接。《白发之书》则指向了李商隐诗中频现的白发意象,如“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青草、白发、浮云、扁舟,与夕阳、寒蝉一类悲凉衰微的意象相似,在微观的层面上,是诗人敏感细致的生命体验。
《李商隐的艺术家画像》由此串联起多个李商隐式的意象与情景,由眼下的画像至远处的夕阳与黄云,将个体生命投射在自然变化之上,以浮云烘染生命短暂、世事瞬息万变之意。末句“一分钟的绚烂是一分钟的灰烬”,传达了对于繁华与衰败更替、生命之灿烂又短促的黯然神伤。逝者如斯,裹挟其中的是人类短促的生命,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在《说到就要做到》这首诗中,赖特写道:
在寺庙的一声钟响中,这个僧人可以听到
过去与未来的一切,
从针尖上,他可以剥离出一整个世界。
或者将世界的无边无际磨成一粒麦子的大小。
那些是他的脚印,在禅院的墙边。
这里糅合了李商隐诗《题僧壁》“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四句的意象,并颠倒了原来的由视觉至听觉、由空间至时间的顺序。前两句表述了一种大与小的辩证法,即“芥子藏须弥,须弥纳芥子”的禅理——在这种无限与有限的转换中,兴衰荣辱显得微不足道。李商隐诗《送臻师》也有相似的感触:“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后两句则审思了时间的主题,前世、今生、来世,古今兴废,皆在一声钟鸣中,这是对于永恒与瞬间的体认,具有终极意味的思考。在如此的时空尺度上,人生之短暂、微小显得尤其突出,赖特借此表达对于生命之短暂的喟叹。
如果赖特关注的是李商隐诗的哲学意识,那么美国诗人罗伯特·凯利则聚焦其中的爱情主题。他的一首题为《落花》的诗,将李商隐的同名诗歌《落花》以诗句的方式嵌入关于现代爱情的描述之中,叠加了多重的情感经验。不过,相似的离别,李商隐的“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变成了一片片撕碎的照片,其中的怅然若失被移置到现代爱情的现场,而唐诗中焚香的缭绕香烟,变成了烟草的烟雾:
这是我们冬日的故事,
放凉的茶,我们的宝利来照片
撕碎了散落在地板上的闪亮的花瓣,
在熄灭的壁炉前。
这里将李商隐式的美学融入诗歌创作。不过,李商隐的《落花》情感深沉,将落花的凄凉与落寞接榫于晚唐的文化气质之上,贯穿了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内心情感。凯利的理解则是取其一端,描述了爱情的一面。
李商隐诗中的怅叹有着历史的纵深,交织了人生的聚散离合、年华的短暂易逝以及社会的沧桑变化,往往从眼前之景,延伸为对于人生与时代的体认。不过,李商隐也具有超越时代的感染力,表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仍具有表征当代人生经验的效力,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可以生成新的诗境和审美意涵。在诗歌的跨文化旅行中,李商隐的诗也变成了满地的落花,被异国他乡的诗人捡拾起来,点缀了不同的诗意。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6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