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文坛述往】
作者:肖亦农
他真的来看我了。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少敏在信中说,他要来内蒙古看我。他在天津,我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那时的伊克昭盟交通极差,既不通飞机,又没有铁路,人们坐火车到达包头后,再转长途客车,途中还隔着条黄河。黄河上没有公路桥,人畜车辆过往得过浮桥,可谓“隔河千里远”。所以,少敏说要来看我,我觉得关山迢递的,他也许只是随口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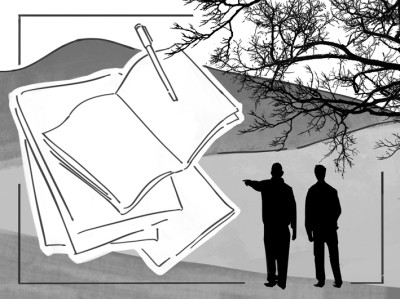
插图:许馨仪
少敏从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便与编辑部联系,得到了我的地址。于是我收到了他的来信。看到那清秀的字迹、滚烫的问候,他那浅浅的笑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
十余年前,张少敏是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大朋友”。少敏不是知青,而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用他的话说,那更是一个无着无落的群体。当时,他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在兵团的报社当记者。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知青,在一个团的政治处当报道员,少敏来团里采访,我总是颠颠地跑前跑后。后来熟了,我才知道他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顿生敬意。当时,报社常组织各种形式的改稿班,特别善于发现青年作者,我算是一个,经常被请到报社改稿。
记得那天下午,少敏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谈稿子。他正在阅稿,见我来了,微微一笑。他的微笑是那么亲切,就像一位大哥哥。少敏给我倒了一杯水,和我说起了稿子,大意是写得不错,有些文字上的小毛病,他已经处理完了,可以见报了,我听了很高兴。聊着聊着,我突然被窗外的一株杏树吸引了,那是四月天,满树都是粉红色的杏花。这些年我在大沙漠里,哪儿见过桃红柳绿,便随口说了一句:“三年未见杏花开了。”少敏听完,认真地看着我,说:“小肖,你的语言挺有文学性,我觉得你是写东西的料。”我听了,心怦怦跳。其实,我一直怀有当作家的梦想。后来,我又试着写了几篇东西交给少敏,都在兵团的报纸发表了。可以说,少敏是将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特殊的历史时期,少敏曾因为处理我的一篇稿子与上级争论了起来,作品最终还是没能发出来。他对我说:“这是一篇好东西,千万别灰心,耐心地等一等再看。”他依然是微笑着对我说,那笑容历历在目。
后来兵团解散了,曾领着我们扎根边疆的现役干部全都返回了部队,听说少敏那批解放军大学生去了军事院校。而我,几经辗转留在了伊克昭盟的交通部门,当了一名公务员。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对方半点音讯。
改革开放后,我们步入令人激奋的属于文学的时代。我又开始写文学作品,我要圆自己的作家梦。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少敏的来信,才知他从军队转业到天津市作家协会了,在《新港》杂志社工作,当小说组的组长,他还热情地向我约稿。《新港》是圈内知名度挺高的文学期刊,一个身处荒山野岭的文学青年,得到这样的邀约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连夜赶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稿子,天一亮就跑到邮局寄去。十天以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少敏告诉我,在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火车上了,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果然,第二天下午,少敏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的脸上还是我熟悉的笑容,我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少敏让我带他去宾馆,我说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我热情地把他带回家——这是伊克昭盟人的待客之道。
当晚,少敏就睡在我的小书房里,我俩说了半夜的话,有无限感慨。他鼓励我好好写东西,他认为我的文字有幽默感,这是成为好作家的必备条件。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写作要有幽默感。少敏在我家,常抱着我刚满月的儿子转来转去,还同我谈着梅里梅、茨威格、海明威,儿子瞪着大眼睛似乎也在听,偶尔会尿在少敏身上,少敏仍是微微地笑着。那次少敏给我开了个书单,原来还有那么多我未看过的书。
后来,我俩合作了十部中短篇小说,发表在《十月》等文学杂志上,百花文艺出版社还为我们出版了一个集子,蒋子龙作序。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因为商量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我住进了少敏的家里。我俩吃着少敏夫人切的冰西瓜,谈得热火朝天。我俩还曾住在一个宾馆改稿子。正值刚供暖的日子,暖气不太热,我半夜醒来,见少敏躲在卫生间里写稿。少敏指着手里的稿子说:“有个地方,我还想动动。卫生间里的暖气稍微热点儿,在这写也不影响你休息。”少敏的体贴让人鼻子有些发酸。
1987年,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内蒙古文联举办了“春之声”笔会。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铺开稿纸,鬼使神差般,我在题头竟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篇献给我的良师益友张少敏。”小说发表在《火花》杂志上,这句话一个字都没有动,我挺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小说被《新华文摘》转载时,题头这句话仍保留着。后来,少敏成了内蒙古作家的朋友,哈斯乌拉、邓九刚、路远、乌雅太等人都有作品发表在《天津文学》。
记得1988年初春,我和少敏应邀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剧本《红橄榄》,在北影厂的仿清楼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少敏已担任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总有忙不完的事。为了改剧本,他特地请了创作假。少敏告诉我,一定要抓住原小说的神韵,保留原小说的故事。我俩一场戏一场戏地过,耐心地打磨着。责编赵海城有时会来询问进度,少敏总是回复,我们还在打磨几场重场戏。他对我说,咱不满意决不交稿。有时写累了,我俩就跑到《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家打扑克,一起去的还有老同学田增翔,其乐融融。有时玩到深夜,我和少敏走夜路回到北影厂。夜晚静悄悄的,马路上空无一人,我俩会高喊几声,然后哈哈大笑,放松自己。时而有朋友来看我们,比如梁晓声。我们也去晓声住的筒子楼——即使是大白天,也得在走廊里摸索着前行。我挺佩服晓声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创作出那么多鸿篇巨制。那时柳溪也在仿清楼里住着,修改《燕子李三》的剧本。有时少敏跑回天津处理单位的一些事情,我写累了就去柳溪房内聊聊天。《红橄榄》的剧本完成了,交给电影厂时竟然一稿通过。记得当时北影厂文学部的王主任对我们说,一稿过,北影厂建厂以来很少有过。
后来,我去北师大读书,少敏依然在天津市作协,各忙各的,一晃就进入了新世纪。
今年初春的一天,我接到少敏夫人的电话。我赶忙叫了声“嫂子”,说多少年了,我一直记着你的冰镇西瓜呢。嫂子低声告诉我,少敏走了。
我放下电话,万千往事涌上心头,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个世上一个懂我、知我的人走了,我的如师、如兄的好朋友走了。我翻开影集,想找出我们的合影,竟然一张都没有。我记不清和少敏是否合过影,但他那浅浅的笑,将留在我的心间,直到永远。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1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