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作者:张涌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著作《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古代文献,就是四大文明交汇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见证。

人物素描:卢重光 绘
从文献整理到残卷缀合
杭州与敦煌山水相隔,但浙江学人与敦煌学有着不解之缘。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等前辈学者的引领下,20世纪80年代起,我与敦煌学结缘,对敦煌写卷中的俗字、俗语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又醉心于敦煌文献的整理校勘。20世纪90年代,我牵头的学术团队开始了敦煌文献的大规模整理工程——《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在对敦煌文献全面普查、系统分类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不少残卷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有些是可以拼接复原的。如敦煌文献中有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残卷数十件,分藏于中、法、英、俄各国,我们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共发现42件玄应《音义》写本残卷。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42件残卷包括第一卷4件、第二卷6件、第三卷11件、第六卷12件、第七卷1件、第八卷2件、第十五卷1件、第十六卷1件、第十九卷1件、第二十二卷2件,另摘抄1件。最后比较行款、字体、纸张、正背面内容,结果发现存有2件以上残卷的一、二、三、六、八、二十二各卷均全部或部分可以缀合,总数达32件,可缀数超过四分之三。这些原本撕裂的残卷不宜仓促分头整理,而需要先拼接缀合,才能在类聚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的整理成果。如敦研357号残片,存8行,无题,《甘肃藏敦煌文献》编者拟题为“字书残段”。其实此残片并非字书,而是玄应《音义》卷二残文。后来我们发现此残片与斯3469号残卷字体、行款完全相同,盖出于同一人之手,应为同一写本的残片,可以拼合,而后者《敦煌宝藏》定作“一切经音义”,甚是。此二号拼合为一,进而比勘刻本玄应《音义》,不但可据以纠正刻本的文字之误,而且可以得知敦研357号第六行行末“足大”二字及其下的半字(“大”下尚有小半字,存上部,应为“指”字)应移至第八行“古才反”之后,盖碎片误粘于前,“古才反,足大指”是对第八行“脑胲”之“胲”的音释,而第六行下部本身原有残损,误粘的碎片复位后,所存字句与玄应《音义》卷二相关文句完全相同,残文怡然理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体会到,敦煌文献中残卷的比例极大,残卷缀合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确实非常重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6年,《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整理编纂工作大体完成后,我开始把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残卷缀合方面,并先后发表了《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敦煌本玄应〈一切经音义〉叙录》《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等讨论残卷缀合的论文,为残卷的大规模缀合作了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可缀残卷数量巨大,除了团队核心成员外,我还先后指导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加入敦煌残卷缀合的队伍。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就是我们学术团队师生共同倾注心力打造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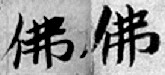
敦煌残卷缀合的方法
如众所知,敦煌文献数量浩繁,总数达七万号之多,而且流散后分藏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数百个公私藏书机构。要在如此庞大且分散的收藏中找到两个甚至十几个可以缀合的残卷,确实如同大海捞针,难度极大。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在几十年研读、整理敦煌文献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体会到残卷缀合对深化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性,完成此项艰巨任务的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幸运的是,我们的前辈学人已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馆藏敦煌文献影印本的陆续出版,为人们阅读敦煌文献带来了极大便利,也为敦煌写卷的全面缀合创造了条件。在具体实践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首先,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分类,把同一种文献或内容相关的文献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同一文献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因为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通常比较大;最后,比较行款、字体、书风、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
这里我想举一个具体例子来作说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共51号,其中WB32-1(31)号仅存1纸19行(前部另有一行,但仅存上栏末字左下侧一个残点),每行分上下两栏,每栏抄一佛名。原卷无题,木盒装,盒盖表面墨书“佛说菩萨念诵三昧经卷苐六”,此题与写卷内容不符,当系误置。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三)》改题作“佛名经断片”,大抵可行。考卷中有“从此以上二千一百佛十二部经一切贤圣”文字一行(第17行),这是只见于敦煌文献及少量日本古写经中的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统计佛名数量时的典型句式。循此线索,我们对敦煌文献中的所有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写卷作了全面普查,共发现该经写卷近700号。进一步比对发现,此页残纸内容出于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卷三。敦煌文献中有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卷三写卷24号,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博物馆、英国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日本杏雨书屋等6个藏书机构。仔细核对发现,日本杏雨书屋藏羽485号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卷三第18纸与第19纸之间掉了一纸,而国会图书馆WB32-1(31)号正是羽485号丢失的一纸(见下大图)。羽485号首尾完整,存31纸,每纸19行或20行,与WB32-1(31)号所存一纸行数相合,二号行款格式、字迹书风近同,卷中统计佛名逢百整数的一行文字上方皆绘有一尊彩色佛像,而且WB32-1(31)号首行之前所存一字的左下侧残点,正是羽485号第18纸末行上栏“南无宝上佛”句末“佛”字左部撇笔残缺的末梢,拼合后此字可成完璧(见下小图),二号缀合后,WB32-1(31)号得以与原卷团圆,羽485号第18与第19纸之间丢失的一纸亦得以复位,从而形成《佛说佛名经》卷三(十六卷本)又一完整长卷,WB32-1(31)号堪称一纸千金。曾有日本敦煌学前辈断言包括WB32-1(31)号在内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敦煌写卷多为“赝品”。今WB32-1(31)号既可与可靠性没有异议的羽485号完全缀合,则其为敦煌写经亦可得以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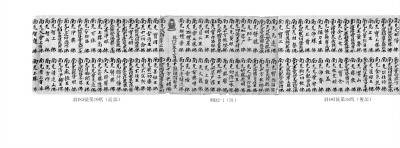
进展与期待
20年来,我们的学术团队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文献作了穷尽性的调查和数字化,建立了数据库,并给其中四千多号未定名残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献的家底。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所有敦煌残卷展开了大规模的缀合工作,新发现可缀合残卷近万号,同时纠正了前人在定名、断代及属性、字体、真伪判定方面的大量疏失,有很多创见和发现(包括对敦煌藏经洞的性质提出了全新观点),最终成果将汇集为约800万字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更为可喜的是,我们把项目推进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参加本项目的博士、硕士生、本科生已有六七十位,他们毕业后分别去往全国各地高校工作,有的已成长为青年学术骨干,有关成果将集结为“敦煌残卷缀合整理研究学术书系”陆续推出,包括《〈大般若经〉敦煌写本研究》《〈金刚经〉敦煌写本研究》《〈金光明经〉敦煌写本研究》《〈八阳经〉敦煌写本研究》《〈大般涅槃经〉敦煌写本研究》《敦煌四部文献写本缀合研究》《敦煌佛经文献写本缀合研究》共7部,真正做到了出成果、出人才,薪火相传,为敦煌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
从2007年第一篇敦煌残卷缀合的论文发表以来,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近20个年头。据调查,敦煌文献中可以缀合的写卷达到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敦煌文献的总数是七万号,那可以缀合的写卷就达到17500号左右。我们目前发现可缀合的,仅比这个数字的一半略多一点,主要聚焦于四大藏家及其他部分已刊布图版的公私藏家的藏品。事实上,还有大量公私藏家(尤其是日本)的藏品没有公布,这部分散藏藏品可以缀合的残卷比例更大,缀合难度也更大,需要我们付出更艰苦的努力。迄今为止,我们的工作都是依靠“人脑”,是一个一个卷子翻阅、比对的结果,花的是笨功夫,是汗水和心血熔铸的结晶。佛教徒把佛经的抄写、修复视为一种功德,敦煌残卷的缀合同样可以作如是观,再苦再累,我们也无怨无悔。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敦煌学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研究方法。我们期盼着所有公私机构收藏的敦煌写卷的尽快公布,也呼唤人工智能给敦煌学研究安上智慧的翅膀,助力敦煌残卷缀合研究,让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拼接缀合,重现千年前的模样和风采。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5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