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点击浏览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浏览器请点击“ ”按钮
”按钮

【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段爱松(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昆明文学院原院长)
如果要给漂泊的云彩选一个故乡,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云南恐怕是最适合的;如果要给文学寻一个根脉,那么对于我来说,彩云之南,便是最能净化肉身和荡涤灵魂的诗意栖息地。
在云南昆明晋宁,一个名叫晋城的小镇上,我常常和童年时的小伙伴到象山上玩。象山的风很奇怪,有时感觉很大,有时感觉很小,有时感觉它并不存在,有时又感觉无处不在。不过,正是这种时大时小、时有时无的风,像一双无形的巨手,搓揉着天空。于是,天空就像着了魔法一般,变幻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云彩。
我无数次看着这些变幻莫测的云彩出了神。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这些云彩或许并不是真的云彩,而是童年身体内奔涌不安的血液,就像象山脚下映山塘的水,被天空的重量压得越来越低。这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说能做什么。
除了在晋城最东边的象山上,能如此感受这般云彩外,还有最西边阔大的水稻田间,一条清澈的杨柳河,从中哗啦哗啦贯穿而过。站在长满杂草和野花的老土埂上,我似乎能感受到,那些着了象山魔怔的云彩,一堵又一堵,一团又一团,一片又一片……如同不知名的浩大乐音,微微倾斜,翻涌跃动,层峦叠嶂,召唤着空旷而古老的天空。这让童年的我感觉到无比惊异,更让我回想起我的奶奶不止一次“吓唬”我的话:小孩子吗,可不能乱动,要乖乖听话,这个地底下,可躲着一个王国的兵马哩……
对,这就是我土生土长的故乡晋宁,曾是数千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滇国都邑,也是伟大航海家郑和的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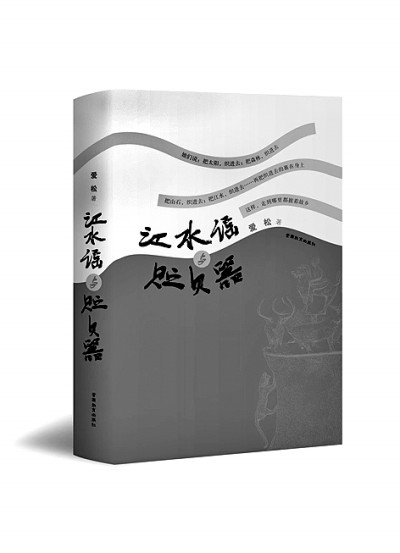
后来,我在梦中见识到,那些深埋地底的古滇青铜器上的太阳纹,纷纷幻化成小镇上空云彩的样式和颜色。它们变化成无数模样,四处出击,拼命地找啊找,但不知究竟在找些什么。这些诡谲的线条、纹路和样式,甚至还发出奇妙的无声之音。
这种只可留存在记忆中的乐音,长久回荡在我童年的脑海,像是一道来自远古的无声密令抑或召唤。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少时的我抱起吉他,在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传统院子的石桌子旁练习弹奏,同时,也写下真正意义上的一组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手记》,“阿德莉塔,指向故乡的一切中/没有你,停下脚步匆匆/瞥见路和天一样高远”。从那时起,西班牙古典吉他大师泰雷加琴弦下的“阿德莉塔”,及其暗喻的一切美好女性形象,都活脱脱幻化成为故乡晋城上空,那些变幻莫测而又隐秘明亮的轻盈轮廓与色调。
我的故乡晋城,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小镇,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在这片或许如我奶奶所说的,埋葬着一个王国兵马的古老土地上,作为一个弹奏者和写作者,又将如何用音乐和文字接续传统、现实与未来?
2009年的秋天,当完成吉他名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的同名长诗时,我才意识到,从童年到少年,再从少年到成年,故乡上空的云彩,一直指引我的归乡之路。哪怕求学和工作在外,历经多少困苦与欢乐,也改变不了一个人血脉中最纯粹的底色。就像真实的阿尔罕布拉宫,对于古典吉他大师泰雷加;一如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对于我这样一个生长于小镇的练习者。
或许因为出生地缘的特殊性,我养成读史书和地方志的习惯,并反复翻阅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传》。那段时间,甚至还将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四集纪录片《消失的古滇王国》找出来,翻来覆去地看。就像一个被遗弃许久的游子,试图从中找出点线索,哪怕是找出一丝破绽,也会欣喜万分。可我要找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故乡上空的云彩一定知道,因为它们也在四处寻找,它们要找寻的,或许就是彼时的我,坚持练琴和写作的意义和答案。
看史书看纪录片不过瘾时,我还常邀约朋友一起去晋城石寨山。记得是在1955年3月,云南省考古工作队进驻石寨山,进行第一次试探发掘,但直到第二年11月的某一天,考古队第二次发掘时,第六号墓底漆器粉末中的泥团,被学者孙太初先生用颤动的手心捧起。用毛刷清理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闪着金光篆书的“滇王之印”,尘封两千多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这完全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随后,一批又一批青铜鎏金贮贝器,顺着这道时间裂缝挤蹦了出来,其中有一尊非常独特神秘,我命其名曰“金色骑马人”。
“我已多年未见到过他。贮贝器上,他骑着青铜色的牝马,四周围满了耕牛,两只锈迹斑斑的豹子正从地底飞蹿而上。我知道,他们都饿极了。他们在苦苦寻找,一身金黄色的衣帽,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因为这座青铜贮贝器,几乎不假思索,我就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缕曲》开了这样一个头。而我不断去石寨山考古现场,就是想看看这尊像是在逃亡的“金色骑马人”,在漫天的历史迷雾中,因何逃亡,又将逃往何方?
诗人海涅说过:“语言停止的所在,就是音乐的开始。”故乡出土的一件件精美青铜贮贝器,多像是被时间凝固的一曲曲无声古老歌谣。这和我在象山上看到的那些云彩,何其相似!地底和天空形成的这种奇妙维度,既打破物象之间的藩篱,也打破艺术表征的逻辑,回到作为存活天地间“人”的本质性存在,以及与“人”关联的所有已知和未知。就像诗人、作家邱华栋所言:“其实只存在一种文学,就是关于人的文学,关于人的心灵在时代和历史中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在弹奏《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还是在写作长诗《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无论是通过爬石寨山、逛博物馆、读地方志、看影音资料来熟悉贮贝器,还是据此昏天暗地敲击键盘写作长篇小说《金缕曲》《异梦录》等,似乎都是为了某种人性的探寻与回归。就像故乡的云彩,它们一定有着人类温润的奇梦妙幻,否则,就不可能在一个练习弹奏和写作者的大半生中,带来那么多丰盈的哀伤与天真的敏感。
当然,故乡也是变化着的。这种变化,并非单纯来自时间、空间或阅历的叠加,而是有一天,我发现云彩突然有了重量。这种重量和之前感受到的无声之音,如出一辙。它是一种无重之重,甚至比你用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实际重量还要重。这种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012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赶回故乡晋城,重走故乡童年路,被夕阳染得通红的云彩,瞬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过往,审视周围一切,甚至审视未来可能发生的梦境。于是乎,有关故乡历史、现实甚至是想象的离散的人和事,如同最为浩大的喷薄云层般,不断冲击撞痛着我,令我写下《金缕曲》之后,仍在延续“晋虚城”谱系的建构。诚如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所说:“小说创作就是把异质的和离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种一再被宣布废除的有机关系。”云彩获得了心灵被现实激活的重量的同时,我也获得这种重量赋予的命运启示:“有自己独到的异域之境,就应该写出不一样的小说。”并从纵向维度上,连续写下《西门旅社》《通灵街》《招月》《蓝波》《元音》等一批“晋虚城”小说。
与此同时,一如云彩的无端变化,非虚构写作,从我诗歌小说的缝隙中,强劲地横切出来。我的文学故乡,沿着中心“晋虚城”,像一棵榕树的根系,跟随云彩的流动,在云南大地蔓延开去。

晋城俯瞰 宋绍华摄/光明图片
2015年,仍是一个秋天的清晨,我来到我的姓氏族亲故乡大理。我身体里有着多民族融合的血液,以至于我的写作,很大一部分和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息息相关。通过对大理洱源郑家庄几个月的亲历体验和调查走访,“七个民族一家亲”让我深受感动与震撼。在长篇报告文学《云南有个郑家庄》里,我记录过第一天到达时的感受:“顺着朝阳蓬勃向上的力量,我在郑家庄四周群山叠嶂间,感觉到了某种神圣的护卫之力。空气和流云,催动着这些静止的山峦,就像一艘艘巨大的船待命远航,想必它们承载着郑家庄以及四周村落未来的命运和希望。”是的,在碧蓝天空中那些依山环绕的云彩,宛如一个个隐身的巨人,护佑着这个远近闻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2019年,因为采写反映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我三次深入偏远的怒江州独龙江乡。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在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险峰上,无数的云彩,像在牵引着那些皑皑白雪,我行我素自由奔跑;还有晴空下,独龙江缓缓流淌过迪政当村,这些由积雪融流汇集的透亮脚印,在天光透过云彩的折射下,不停变幻出数十种色调……此情此景,瞬间激活通达我在象山看云时的童年。还有独龙族文面女脸上奇诡的暗青色图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种突如其来的色调和线条,宛若梦境中神秘的云彩。想必它们该是某种庇护天地的古老巫术,竟如此秘而不宣却又撼人心魄。
正是彩云之南,西南之境的故土、历史、自然……成为我文学创作的源头,也给了我写作道路上融合开阔、纵深探索的勇气。一如我刚出版的长诗集《江水谣与贮贝器》,独龙江和古滇国跨越时空,奇妙地相遇了。也如我的长篇小说《闪亮的星河》写到的,一代又一代为边地献身的战士,存活在云南各民族同胞的记忆中,不仅是夜空最闪亮的星辰,也是晴空最灿烂的云彩。
我想,在云南神奇的土地上,文学伟大的传统,也应该像伟大的同乡航海家郑和,用一生漂泊经历的风浪,为彩云的故乡,也为历史的天空,画下冒险却永恒的航标。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5日 14版)
